「原來如此,有志回報家國,不愧是季大將軍教導出來的,」她眼含笑意,看向季文牧,「姐姐尚且如此,也難怪他敢在宮門口舌戰眾臣。」
「她算我哪門子姐姐?」季文牧和她鬥嘴。
我突然明白了她叫我來的意思。
季文牧在宮門口和群臣吵架的事我也知道,當初先帝駕崩太過突然,凰月登基倉促,根基不穩,那時外敵趁勢來犯。
群臣各懷心思,欺凰月年幼,內憂外患。
季伯父請旨退敵,而季文牧也在季伯父請旨那天的散朝時辰,站在馬上,將眾臣禍心廣而宣之,不等他們告狀,便向凰月請罪,說他冒犯大臣,自願前往戰場,讓凰月看在季家男丁都在戰場的份上,免去季家老小之罪。
凰月無不應允,言眾臣都是深明大義之輩,不僅不會和他這個小孩計較,反而會關照季府。
眾臣被擺了一道,吃了這個悶虧。
那日我本想跟著季文牧一起去,他冷著臉,難得強硬地將我關在府里,還讓一眾府兵在門外看守著我。
我無意識地咬著手中的烤雞,有些燙,嘶了一大口氣。
他為她守國,她為他護家。
他們之間的羈絆遠比我想的還要深。
凰月這次叫我來,就是特意告訴我這些的嗎?
」柳將軍,可曾婚配了?「
我愣了一下,」尚未。「
「這不大妥,柳將軍為國效力,豈能讓終身大事毫無著落?」
「季伯母在操持著了。」
「季夫人所見終是少了些,不若朕在文武百官家中挑選,為將軍擇一合適夫婿?」
我張了張嘴,季文牧忽然插了進來,「小月,你怎麼和我娘一樣非要管著她嫁人,她高興不就好了?」
凰月嗔了他一下,威嚴地帝王也流露出幾分小女兒的嬌態,「你一男子懂什麼,女子年華有限,趁早成親,生兒育女方是圓滿。」
我垂眸大咬了一口雞肉,沒有顧及吃相。
凰月又說,「柳將軍女中豪傑,洒脫不羈,定有不少兒郎心嚮往之,文牧你少攪和,壞了好事我要拿你算帳。」
雞肉咬進嘴裡,竟讓我有一股嘔意。
我捂著嘴逼著自己咽下去。
這時,一抹亮光刺痛我的眼睛,我下意識拔出腰間長劍擋上去,嚓的一聲刺耳的響聲,一支長箭被我斬落。
「有刺客!」
季文牧在我身旁吼了一句,迅速護著凰月退開,我立在原地,來不及退開,渾身的力氣仿佛被抽掉一般,身上甲冑如有千斤,手中長劍連握穩都艱難。
士兵很快趕了過來,和刺客戰成一團。
我感覺到我狀況的不對,下意識看向季文牧,他將凰月牢牢地護在身後,像是一個守護神一樣立在她身前。
心中一空,但容不得我多想,我兩手握劍迎敵,瞬間長劍就被挑落到地上,倉促躲避下,喉間被劃出一道血線。
「阿珉!」
我聽到季文牧叫了我一聲,大腦也開始眩暈起來,似乎有什麼東西沉甸甸的,在拖著我下墜。
我甩了甩頭,努力讓視線清晰起來,模糊中看到他高大的身影庇護著嬌小的姑娘。
接著身體不受控制地向前踉蹌。
痛感尚不十分劇烈,胸前貫穿出來的滴著血的劍刃卻極為刺眼。
我瞪大了眼睛,嘴徒勞地張大,只能發出一些低啞的嗚咽。
刺客將劍拔了出去,痛感這時才真切起來,那處傷口似乎都通了風,涼風颯颯地往裡鑽,穿過我的身體。
渾身好冷。
我感覺自己要交代在這了。
卻交代的不明不白。
我怎麼會就這樣死了?
沒死在戰場上,反而死在這裡?
我看向季文牧,他似乎也不明白,怔怔地望向我。
我對著,連動動手指都費力,他像我這走了兩步,卻沒有過來。
「文牧,別離開我。」
耳邊聽到的最後一聲是凰月的這句話。
心中響起來的是那四個字,「小爺罩你。」
10
傳說人將死之時,眼前會浮現走馬燈,回顧平生。
我回望自己的二十三年,見到許久未曾謀面的父母,見到欺侮我的地主,八歲的年紀太小,那時的記憶一閃而過,接下來便是季文牧,各種各樣的季文牧。
我清楚地知道若要放棄十五年的感情必定經歷宛如割肉一般的痛楚,我遠沒有自己想像中那般洒脫,可以說放下就放下,只是現在,腦中思緒當真清明無比。
我喜歡季文牧,是因為他在我最需要安全感的時候以守護的姿態給了我承諾,而事實上,他有更重要的人要保護。
季文牧心中有江山,有大義,有想守護的人,而不是被困在情情愛愛的一畝三分地,糾結我和他是不是兄弟。
我也是。
可惜,浪費了十五年,現在想開了,卻已經遲了。
我想過我會怎麼死。
娘一直和我說要保護好自己,但在她被逼死後我連走出地主家柴房的自由都沒有,那時我想,我應該會餓死在這個只有柴草和老鼠的地方。
上戰場之後,我想,我隨時會死在一柄刀下,一桿槍下,死在戰場上。
回到上京後,我想,也許我會平安順遂地老死。
結果出乎我的意料,有些憋屈。
......
我睜開眼的時候,真以為自己死了。
是一個俊秀的公子叫醒的我,他的眼眸清澈,好像盛滿了水。
「柳將軍。」
他喊了我一聲,我想起來他是誰,是那個要送我回府的小大夫。
我張嘴,只發出難聽的音調。
他和我說,「將軍傷到了嗓子,這些日子不要說話,好好養著,以後還是可以說話的。」
他給我換了脖子上的藥,喂了我喝水,做起來極為熟練。
我拉過他的手,在他的手心上寫,「怎麼是你?」
我不是在獵場嗎?就是被救也該是太醫診治我。
他似乎怕癢,手指蜷縮了好幾下,「我聽聞將軍受傷就來府上看望,太醫們都束手無策,但我想試試。」
他的醫術這麼厲害?
許是看懂了我的眼神,他笑得有些靦腆,「我曾被擄去過土匪窩,那裡的老大留著我給他們看病治傷,他們刀口上舔血,我治的多了,對於這種傷情有些許經驗。」
我又給他寫,「多謝。」
他搖了搖頭,「我去叫季夫人和小季將軍。」
在他起身前我拉住他,他不解地回頭望向我,我環顧四周,這一切的布置對我而言都十分熟悉,卻又很陌生,在他的手心裡一筆一划寫下,「這裡是哪裡?」
他迷茫了一下,蹙起眉頭,「柳將軍,這裡是您的府邸。」
季伯母來看我時眼睛是紅腫的,她抱著我一頓哭,後悔她不該讓我去從軍,我艱難地露出頭,對上季文牧的視線。
他沉默著,和我對視一眼就垂下了眼睛。
梁濟在旁邊說,「季夫人,柳將軍傷勢漸好,但是......」
所有人都看向他。
「她似乎忘記了一些事情。」
「忘記了事情,忘記了什麼事?」季伯母看著我,「珉珉還記不記得我?」
我點了點頭。
梁濟說,「大多是沒有忘記的,但是她忘了這是她的府邸,什麼時候,為何搬進來,這些不記得,約莫還有一些其他,但是柳將軍現在不能說話,還不清楚。」
季伯母又抱著我哭起來。
我倒是沒多大感覺,忘記了的事情似乎也沒什麼重要,便反過來安慰季伯母。
季伯母和梁濟走後,季文牧沒有走,他來到我的床前,卻是一言不發。
讓我有些懷疑,是我啞巴了還是他啞巴了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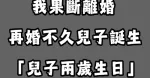
 武巧輝 • 7K次觀看
武巧輝 • 7K次觀看
 楓葉飛 • 4K次觀看
楓葉飛 • 4K次觀看














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