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扯了扯他的袖子,在他手上寫,「究竟是怎麼回事?」
我看到他的喉結滾動了一下,聲音極低極啞,好像很久都沒有說過話。
「朝中有孽黨留存,在守衛里安排了他們的人。」
我點了點頭,稍動一下,脖子還是疼,我便皺了皺眉,嘶了一聲。
他突然抬起手,食指挨到我的臉頰,將碰未碰。
「阿珉。」
他終是收回了手,聲音顫抖起來,「原本該是我吃那塊雞,該是我中藥,該是我......」
我在他手心裡一筆一划地寫,「這又不是你的錯。」
他蹲了下來,高大的身軀驟然變小,伏在我的床頭,將臉埋在我寫字的手裡,我感覺到我的手心逐漸濕潤。
真是越活越過去了,七八年沒見他哭過,他何時這麼脆弱了,我這不還沒死。
「你差點就死在我眼前。」
他低聲說,語氣中含著深深的後怕和自責,「我居然沒能救下你。」
我抽出手,拉過他的手掌,寫道,「你的職責是保護陛下。」
想了想,我繼續寫,「決定參軍的那一刻起,我就將生死置之度外了。」
11
參軍的原因我不記得了,但我記得昂揚的戰意,失敗的頹靡和勝利的呼喊,我完全融于軍旅生活里,沉浸在士兵這個角色中,我見證了無數同袍的死亡,也早就將自己的生死一併交付出去,原因已經不重要了。
季文牧的眼睛很紅,他問我,「你,參軍的原因究竟是什麼?」
我想了一會兒,寫,「回報家......」
他直接握住了我寫字的手,一眨不眨地望著我,眼中充斥著緊張和認真。
「不是因為我?」
我愣了一下,睜大了眼睛。
「你哪來那麼大魅力?」我看了他一眼,他的目光緊盯著他的手心,分辨我寫下來的字。
我最後一筆寫完,他看向我,眼眸濕漉漉的,被眼淚沖刷得很乾凈,含著一些不解和莫明的抗拒。
「你,忘了什麼?」他的喉結幾番滾動,最後小心翼翼地問我,「你還記得,我,我是你的什麼人嗎?」
「記得你,你是季文牧,」我寫,「是我從小到大最好的兄弟。」
「兄弟......」他仿佛在喃喃自語,沉浸在他自己的世界裡,「你忘了?」
「忘了什麼?不是兄弟還能是什麼?」
我含笑看著他,他怔怔回望,宛如失神了一般,瞧著我搖了搖頭,嘴角勾起一點點弧度。
「沒錯,是兄弟。」
我有好長時間沒能見到季文牧,因為他和季伯父都因為秋狩防衛不當受了罰,多數時間裡,要麼在皇宮要麼在軍營。
季伯母時常過來陪伴我,給我喂補品,養的我胖了好多。
修養數月,我閒的發慌,梁濟每天都過來給我換藥,還會和我講他遊歷四方時經歷的許多趣事,他在土匪窩艱難求生混成三把手的事聽一次叫我笑一次。
喉嚨的傷好了一些,但是沒有完全恢復,梁濟就建議我先繼續沉默,還可以練練字。
看起來溫和有禮的,說起戳心窩子的話來卻也一點都不客氣。
我的字丑是丑了些,能認出來不就行了。
他的字不同於他的長相,分外洒脫,甚至有些豪放,反而是我認不出來他寫得是什麼。
時間長了,再看到那雙眼睛就沒了一開始的驚艷感,季伯母卻越來越喜歡他,我見這些時日裡,他的臉頰也圓潤不少。
他和我說,「聽聞雁南那處出現了一位神醫,等你的傷完全好了,我就去尋他。」
我看向他,毛筆懸在空中,在宣紙上洇出一團墨。
「不在上京呆了?」
他點頭,「這次來上京,本也是想和城中的杏林高手交流醫術,現今我已有了結論,正巧雁南神醫聲名鵲起,正好去拜訪一下。」
說不清自己心情如何,但感覺他若是走了,日子會無聊許多,但拿什麼留他,他自小便遊歷在外,見識過萬千世界,又怎麼會在一處停留。
我在紙上寫,「若是著急,現在去也可,我的傷已無大礙。」
「不急,和同道交流相比,對自己的病人負責更重要。」
他笑著對我,眼中的那汪水好像要隨著笑意漫出來。
我點了點,繼續垂下頭練字,他湊過來看了一會兒,「怎麼有氣無力的?筆鋒呢?」
我寫,「你又不是先生,還管我寫字怎麼樣?」
他多看了我幾眼,忽然露出了悟之色,沒有說話,出去了一趟,給我端來了一碗紅糖水。
「喝吧,心情會不會好一些?」
對上他善解人意的目光,我也不好意思拒絕,硬著頭皮喝下這碗甜水,最後一口最為甜膩,我擰著眉頭喝下去房門突然被打開,我被嚇了一跳,那一口直接嗆在嗓子眼。
我捂著嘴咳,梁濟給我遞了碗清水,看向門口,「小季將軍來了。」
12
季文牧走過來,我身邊站著的人就換了一個。
我看過去,梁濟站在一旁有些錯愕,他摸著被撞的肩膀,看了季文牧一眼,低頭笑了一聲,對我說,「既然有小季將軍照顧你,那我就先回去了,你不要忘記喝藥。」
我點頭,送他到門口,一回頭便撞上一堵肉牆。
他的聲音在我頭頂響起,「你和他的關係都這麼好了?難不成你又要多一個兄弟?」
我後退幾步,和他拉開距離,拉過他的掌心寫,「不是兄弟,他是我的救命恩人。」
「你不是也救過他,這不就扯平了?」
我想了想,說得倒也對,「那便是朋友了。」
「朋友和兄弟對你而言有什麼區別?」
這有什麼區別,能有什麼區別,這有什麼好區別的?
我眨了眨眼,望著他,寫下來,「對我都很重要。」
他的胸口重重起伏,臉臭起來,接著拉著我回到室內,坐在椅子上抱起了自己的腦袋,垂頭喪氣地說,「娘要給我議親。」
我一聽便樂了,當時他對我見死不救,怎麼就沒想到他也有今天。
我拍了拍他的肩膀表示同情,他說,「我不想去見。」
見一見也沒關係,若是不合適便直接和季伯母說好了,她也不會強求。
但他搖了搖頭,沉默不語。
我一撫掌,忽然想起來他與凰月青梅竹馬的情誼,可他難道想入宮為妃?
不大可能。
這便是癥結所在了,他有心上人,但是卻不能和心上人在一起,甚至不能說出來,也難怪這麼苦悶。
有些難辦,這我也沒有辦法,只能拉著他散散心,便寫,「騎馬去?」
「你的身體好了?」
我對他聳了聳肩,這點傷算得了什麼?往常又不是沒有帶傷上過戰場。
太久沒出來放風了,自打能下床就在書房練字,在廊檐底下喂鳥,我的骨頭都快散了。
一上馬就感覺精神頭起來,忘了是為了給季文牧解悶,不僅騎出了城,還騎到了兵營。
將營里兵器都耍了一遍,府里不是沒有,但梁濟日日看得緊,走快點他都要提醒我兩句,更別說摸到這些傢伙了。
待我興致消減下來,天已經黑了,季文牧說這個時辰城門都關了,我和他便在軍營歇了一宿。
到半夜胸口的傷處就開始隱隱發疼,我沒大在意,第二日起來,痛感便有些尖銳。
我沒和他們說,讓季文牧直接呆在軍營,自己回府。
原本暢快的心情在見到在廊檐底下拿著根草逗鳥的人後蕩然無存,霎時間,不僅傷口在疼,神經瞬間緊繃起來,我似乎忘記了一件事。
梁濟見到我,笑起來,「回來了?」
他走過來,「正巧早上的藥也快要煎好了,你回去換身衣服就來喝藥吧。」
我連忙點頭,錯過他之後就捂著胸口進了門。
傷口疼的有些厲害,但我不敢和梁濟說,不聽大夫的話並不是一件明智的舉動,和大夫對著來更是蠢上加蠢,況且,我現在已經感覺梁濟不像我想像中那樣純良無害,純良無害的人怎麼能完好安全地遊歷各方?
我換好衣服後去找他,見他手裡端著藥便爽快地一口喝下去。
入口一剎那,極致的味道刺激得我頭皮發麻。
怎麼會這麼苦?
苦的想把頭摘下來。
我聽到梁濟的笑聲,他說,「將軍真是痛快人,我還沒來得及說。」
「我問了下人將軍昨日出門的時間,料想你必定來不及喝藥,給將軍配的藥都是按療程算好的,缺了昨日那一碗,今天的就需要做出變動,所以將軍喝到的這碗喝之前的都不一樣。」
苦的我眼淚都不由自主流出來,盈滿了整個眼眶。
「變動倒也不大,只需多加一味黃連,本想提醒一下將軍,但是沒能快過你。」
他歪著頭,好奇地問我,「苦嗎?」
我的臉皺成一團,抽了抽氣,用盡全身的力氣才把嘴裡那一口給咽下去,對著他含淚搖頭。
我不是一個怕苦的人,往常的藥可以一口喝掉,但這碗苦的非比尋常,我花了半炷香的時間,藥都要涼了才堪堪喝完,他到底給我加了多少黃連?
「將軍真是女中豪傑。」
我勉強對著他露出一個笑容,但眼前景象已經被眼淚糊成一片了。
朦朧里他伸出了手,翻過我的掌心,在我的掌心之上放了一個東西。
我眨掉眼淚,看清那枚蜜餞。
「知道將軍不怕苦,也不愛吃甜,但我喂小孩時習慣準備一顆蜜餞,將軍要是不嫌棄,就吃了吧。」
不嫌棄,一點也不嫌棄。
我把蜜餞放進嘴裡,甜絲絲的味道瞬間沖淡了厚重的苦味。
我的眼淚又不由自主出來了。
怎麼會有人不愛吃甜?
以後我最愛吃甜。
「將軍這麼適應,那我就放心了。」
聽到這話,我心裡有了一種不好的預感,立刻拉過他的手,「以後都要喝這個?」
他的秋水眸眨啊眨,「是啊,我方才說了,缺少了一碗,以後的藥都要調整。」
我的靈魂都因為他這句話變苦了。
「將軍英勇無比,傷未好時都能逞現上戰殺敵之姿,區區碗藥,必然算不了什麼。」
他抽回他的手,兩手端正地交織在身前,對我莞爾,一如初見的溫文爾雅。
我卻隱隱看到,他在的那半邊天都是黑的。
13
喝了大半個月的黃連湯,度過了暗無天日的大半月,傷勢基本完全恢復後,梁濟給我端來了最後一碗藥,我已經習慣了這種相處方式,他卻突然和我辭別。
我望著他,一時沒有反應過來,心中便若有所失,「這麼著急離開。」
他只是對我笑了笑。
我嘆息一聲,「你有志向,那我也不留你,只是,日後我怎麼尋你?你也不會一直在雁南呆著吧?」
「尋我?」他似乎有些詫異,面容怔愣,想了想後,說,「我居無定所,想去哪便去哪,以後如何,我也說不準。」
聽到這話,頓覺失落,卻又說不出什麼。
他眼中含笑,眸中依舊純澈,「有緣自會相見。」
我將他送至城門口,他說,「送君千里終須一別,將軍送我到這就好了。」
「別叫我將軍了,叫我柳珉就好,也可以叫我阿珉。」
他的笑意一滯,眼中流露出的情態竟有一種平靜的湖面泛起波瀾的感覺,但這變化太快,就像是錯覺,他依言叫了我一聲,「阿珉。」
我點了點頭,牽著馬,不想看他遠去的背影,便牽緊馬繩想要上馬離開。
「阿珉。」
我轉身看他,他手裡不知何時多出了一枚平安符,表面已經泛白,看起來有不少的年頭。
「我身無長物,拿不出貴重的東西,這是我救治的第一位病人予我的,你......」
我伸出手去,他將平安符放在了我的手心,合上我的手掌,說道,「祝君平安。」
說完便回身上馬,揚鞭離去,沒有多停留一眼。
我將平安福握在手裡,望著他離開的背影,胸中好像被堵了一口氣。
「慢了他一步,竟然讓他先走了。」
沒他聊天解悶,日子果然無聊許多,好在很快我就可以回到軍營,日日訓練,倒也充實,那枚平安符便被我貼身攜帶,偶爾想起便拿出來看看,想他是否已經到了雁南。
他走了一個月後,凰月召我入了一趟宮。
她問我護駕有功,有沒有什麼想要的賞賜,在我清醒後便知她的補品良藥都送到了府邸,自然不敢在求什麼。
來回推拉半天,終於切入了正題,她說,「上次未來得及聽柳將軍的回答,不知你對你的婚事有何想法?」
我心裡一個咯噔,季伯母總算不追著我相看了,為什麼又換了一個人。
我不嫁人還是什麼驚天大事嗎?
「不如朕在朝中為卿擇一門婚事?」
「多謝陛下厚愛,只是臣有志報國,並無成家的打算,若是成親生子,必不能再像現在這樣可以......」
她卻打斷了我,「朝中又並非只有你一名武將,況且現今無戰事,若是這樣耽擱了卿的終身大事,朕也於心難安。」
她頓了一頓,語氣變得意味深長起來,「還是說,卿已有心上人,所以不想被朕指婚?」
這也是個理由吧,我硬著頭皮道,「陛下英明,臣確實,已有心上人。」
凰月來了興致的模樣,轉了轉腰間的玉穗,「是誰?」
是誰啊,我怎麼知道。
腦海里兀的冒出來一個人影,但我又覺得把他說出來不太厚道,有些恩將仇報,況且也找不著他。
不過找不著他是不是就可以當成不想成親的理由?
這廂糾結著,凰月問我,「難不成是文牧?」
我驚了一下,看向她,她笑眯著眼睛,不露出半分神色,「自你們凱旋,文牧就時常在朕耳畔提起你,朕便想,你們並肩作戰,同生共死,有了些情誼也實屬應當。」
「同生共死不假,情誼也不假,但我和小季將軍只有十五年的同袍情誼,兄弟情誼,絕對沒有兒女私情。」
也不能拖季文牧下水,他還愛慕著凰月,怎麼能讓凰月把他指婚給我?
「哦?」
凰月微張眼睛,視線半分不錯地落到我身上,似乎在細細探究我話語的真假。
我露出我最真誠的表情,毫不躲避地任她打量。
半晌,她似笑非笑地望著我,「朕還想為你們指婚,看來差點錯點鴛鴦了。」
額頭布上冷汗,真就差一點點。
我低下頭,隱約間似乎聽到一聲嘆息,悄悄打眼望過去,凰月臉上似笑非笑的神情已經消失,轉而是一種深沉而又複雜的神情。
似乎鬆了一口氣,又似乎被更大的煩惱籠罩。
她就望著高高的宮牆,怔怔出神。
我不敢打擾她,好半天,才聽到她的一聲囈語,「我該拿他怎麼辦啊。」
這一句話顯然不是說給我聽,我亦沒有搭話,她似乎都忘了我這個人,直到被一隻的白鳥驚回神。
白鳥不知從哪樹叢飛出來,一下衝到宮外。
她才想起來身邊還有個我,將怔忪的神情一併斂去,揮手讓我離開。
我行禮告退,她卻又喊了我一聲,「柳將軍,若你極為喜愛方才那隻白鳥,你是會將它精緻地養起來,還是讓它四處飛?」
我轉回身,「回陛下,這要看白鳥是什麼鳥。若是家雀自然豢養更好,但若是鷹隼之類,它們當屬天空和自由。」
「時時有人關照不更為妥帖,放它們獨自在外,它們隨時會面臨危險。」
「陛下說得在理,這要看陛下想要的是什麼,失去獸性的鷹隼便不是鷹隼了,它們已經和家雀沒什麼兩樣。」
瞬間,凰月看起來疲倦不少,似乎被人抽走了精氣神,她讓我離開,我邊往回走邊細細琢磨了方才的對話,忽然驚醒。
她說的哪是鳥啊,她說的是季文牧啊。
14
我好像毀了季文牧的姻緣。
這不是他揍我一頓就能解決的事。
連日被這事搞得寢食難安,我瘦了大半圈,臉也日益憔悴下去。
士兵都以莫名的打趣的目光看著我,還有人賤兮兮地跑到我這裡來,說,「將軍,你這是為誰消得人憔悴?」
腦子一時沒有轉過來,我看了他一眼,聽到一陣熟悉的腳步聲。
「季文牧。」
士兵張大了嘴,「小季將軍?不是說是一個走了的......」
「走了的什麼?」
季文牧將胳膊搭在那個士兵身上,士兵激靈了一下,邊退邊說,「走了走了,屬下去操練去了。」
他落荒而逃,好像身後有洪水猛獸,季文牧瞥了他一眼,轉身看我,而我心虛,不敢和他對視。
「他走了你就這麼難受?」
「什麼?」
「你就這麼捨不得梁大夫?」
「是挺捨不得的。」
他的臉色頓時十分難看,我就更不敢和他說我攪黃了他和凰月的事情,只好旁敲側擊。
「季文牧,如果你是一隻鳥,你是想當家雀被人養著,還是到處飛?」
「什麼鳥?」他壓低了眉毛,顯然沒明白我的意思。本來他就特別高,臉色臭起來,氣勢就更加駭人。
「隨便你想當什麼鳥。」
「我的意思是我為什麼要當一隻鳥。」
這是一個問題,我心更虛了,「隨便聊聊,你不想聊也可以。」
說完我就想離開,剛邁開步子,手腕就被人捉住。
季文牧垂頭看著我,看看我,又看向地面,再看看我。
我抽了抽手腕,沒能抽動。
他看向我,神情認真且專注,「那要看養鳥的人是誰,如果,我屬意她,捨棄些什麼也無妨。」
對上他的視線,我心中一陣哀慟,他居然是這麼想的,意氣風發的小季將軍居然不介意被人豢養。
寧拆十座廟,不破一樁婚。
我是不是罪孽深重了?
「看,看不出來,你還是個至情至性的人。」
他鬆開手,神情莫名黯下去,方才眼中灼目的光也寸寸黯淡,也不知想到了什麼,整個人忽然就被籠罩在陰影里。
「阿珉,你想記起來你忘掉的那些事嗎?」
他看起來很悲傷,看得我也難過起來,我忘掉了什麼不得了的事?可我沒感覺忘掉什麼特別重要的事。
「我忘了什麼對你很重要?你和我說,沒準我就想起來了。」
他忽地輕輕嘆了口氣,憂鬱的不像沒心沒肺的他。
「沒什麼,小月下旨讓神風營去雁山剿匪,你準備準備吧。」
我沒有戴頭盔,他的手朝我的頭拍下來,我也準備好了接受這個迎頭痛擊,可是落到我頭頂的只有一道輕柔的力,不似往常那樣隨意,反倒是有些小心翼翼。
他走後,我摸了摸自己的頭頂,深感他的不對勁,以往他接著身高優勢,總喜歡搭我肩,拍我的頭,力道從來不在意,何時會像今天這樣吃錯藥了一般溫柔。
吃錯什麼藥了?
15
前些年戰亂時,各地匪寇猖獗,近幾年頻頻剿匪,滅下不少勢頭,但仍有留存。
雁山匪首因低調些許,躲過了好些年,但氣候日漸增大,官府圍剿不下,這才上報朝廷求援。
為了解匪寇內部狀況,我們設計了一場送嫁,我就是轎子裡的新娘。
因我是個女子,山匪對我並沒有多大戒心,擄我上山時只束縛了我的雙手。
我唯唯諾諾地被他們牽在身後,視線不由自主地落到身前悍匪的腰間,那別著一把匕首,甚是眼熟。
山匪嫌我走得慢,猛地拉了我一把,我踉蹌之下就撞到了那人身上,匕首被撞到地上,露出完整的樣子,他把匕首撿起來,又推了我一下,「老實點。」
我心裡一個咯噔,這把匕首與我給梁濟的那把一模一樣。
有人嬉笑道,「可溫柔些,嚇著新娘子,小心大當家找你算帳。」
為了不打亂計劃,我壓下心底的那點慌張,低眉順眼,瑟縮地被他們關到一間房內,木椅上攤著條碩大的虎皮。
這時我聽到外面有人說,「這個新娘膽子不小,前些個哪個不是哭哭啼啼的,聽得煩都煩死了。」
了解了,這就開始哭。
哭得越來越響,直到對方心煩,猛地撞門進來,將匕首架在我脖子上,「再哭哭,老子剁了你。」
我便轉為小聲抽噎,「爺,奴家手疼。」
他們一幫大漢,對我下手也沒見手軟,繩子都快勒進皮肉里了。
「等當家的回來就給你解了。」
我抬眼看向他,「爺放心,奴家不跑,奴家本就是被爹娘賣給老財主做妾的,能侍奉當家的這種英雄,奴家心甘情願。」
「那你哭什麼?」
我抽抽嗒嗒又哭起來,「因奴家在出嫁前喝了藥,沒幾天好活了,哪想到如今能......可惜晚了,活不成了。」
我捂著臉,嗚嗚地哭。
他們面面相覷,商量了一陣,有人說,「要麼給她看看?」
「也行。」
他們人都出去,沒一會兒外面就響起匆匆的腳步聲,我捂著半邊臉抬頭,對上一雙秋水眸。
我鬆了一口氣,梁濟已經找藉口讓那兩個人離開。
他蹲下來給我解繩,我低聲說,「混到幾把手了?」
他唇角勾著笑,以同樣的低聲回答我,「說來慚愧,還只是個被捆來的大夫。」
我和他說了我來此的緣由,他剛點頭。
門突然被打開,進來一個身形壯碩的大漢,給地面投下大片陰影。
我本是坐在地上,梁濟蹲在我身前,開門這一聲將我和梁濟都驚了一下。
他反應極快,向我壓下來,我的上身不由向後倒下去。
梁濟攬著我的腰,我和他的臉挨得極近,抬眼就能望進一潭秋水裡,他眨了眨眼。
我的心忽然跳的很快。
「梁老弟,你喜歡這個?」
梁濟把我放開,擋在我身前,「說來慚愧,小弟四處行醫十數年,從未傾心過女子,今日......唐突了。」
這個人哈哈大笑起來,「英雄愛美人,正常,正常。」
梁濟彎腰給他作揖,「這些天來,大當家多有抬愛,只是今日小弟還是有個不情之請,想厚著臉皮請大當家割愛。」
大當家搭上樑濟的肩,顯得梁濟嬌小依人,「自家兄弟,說什麼客套話,女人而已,哪有兄弟重要。」
他轉個了身,一把將我拉了起來,塞到梁濟懷裡,大掌如小山般重,拍著我和梁濟的肩膀,「今晚就是你們的,洞房花燭夜。」
我渾身都快僵硬成石頭,動都不知如何動,短短几息,竟比我扎兩個時辰的馬步還要累。
梁濟遲疑道,「這是否,太快了些?」
「快?不快!」
「婚嫁本該三媒六聘,擇良辰吉日,八抬大轎迎她入門。如今不大可能實現,但小弟還是想盡力給她一場完整的婚宴。」
他鬆開我,再度對大當家彎腰,「請大當家成全。」
大當家這才認真打量我,我低垂著眉眼,任他打量。
「需要如此認真?」
梁濟狀似羞澀道,「一見傾心,便捨不得她不好。」
我愣愣地看著他,他回望了我一眼,眼中含水,雙頰微泛紅,真像是純真的兒郎頭一次陷入情網。
16
大當家不僅同意了梁濟的請求,還直接將這間房讓了出來,留我和梁濟兩人在這裡「訴衷情」。
他一走,整個房間都空了下來,我和梁濟都沒有說話,氣氛安靜到有些詭異。
最後是梁濟打破沉默,「冒犯了,若不這樣做,他今晚就要和你......」
「我明白,事急從權而已。」
這又陷入沉默,我活動了下手腳,受不了這個怪異的氣氛,便問他,「你怎麼被綁過來的,不是去雁南找神醫嗎?」
說完我就後悔,雁南離雁山並不遠,他出點岔子被綁過來也不意外。
「找到神醫了嗎?」
他點頭,又搖頭,露出失望的神色,「招搖撞騙之輩爾。」
我同情地看著他,沒找到想見的人,還被土匪綁了,屬實倒霉。
「梁濟,」我叫他,在他看過來之後低頭摸上手底下的虎皮,「你將我送你的匕首給別人了?」
因那匕首,我還以為他出事了,差點露出破綻。
可他沒出事,匕首在別人手上,反而更叫我生氣了。
「在這。」
他從懷中掏出來,匕首靜靜地躺在他的手上,我便感覺自己的眼睛一亮,那點鬱氣頓時煙消雲散。
「我怎麼在一個土匪手上看到了把一模一樣的?」
「先前被綁過來時確實被搶走過,後來取得了他們的信任,我便要了回來,他卻捨不得,就讓工匠打了把一模一樣的留著自用。」
我點了點頭,掩下心底的高興,打趣地問他,「你是怎麼做到到哪個土匪窩都能混的這麼好的?」
「我是個大夫,他們也需要大夫。」
「雁山又不是沒有其他大夫了,怎麼他就這麼信任你?」
他想了想,摸了摸自己的臉,「許是我長了張讓人相信的臉。」
他是玩笑似地說出口,我聽完竟有些認同,看著他極具有親和力的那張臉,誰能想到他真狠心讓我喝那麼久的黃連,果然人不可貌相。
往事不堪回首。
他出去看了一眼,關上了門,和我說了些他這些時日的觀察,我一一記在心裡,有梁濟在,他們對我放心不少,並未特地安排人跟著我,我得以將地形,防衛點一一摸清楚,在婚期將至時,寨子裡張燈結彩,大當家甚至安排了人送我和梁濟去鎮子上採買。
我見到了偽裝成老頭的季文牧,將準備好的情報塞進攤位里,他低聲問我,「你要成親?」
這都傳出來了?
我一邊詫異,一邊點頭,注意著身後的土匪,梁濟引開了他們的視線,我給季文牧比了一個三。
三日後我便和梁濟在山寨里大婚。
我還以為我這輩子都沒這個機會了,結果因為剿匪,穿上了兩次嫁衣。
季文牧忽然抓住我,眼底宛如醞釀著狂風驟雨,他的聲音壓得極低,「既然知道他們的內部情形,你就不用回去了,留在那裡太危險。」
我回頭看了一眼,梁濟將土匪引得稍遠,我確信他們沒有注意到才放下心來,飛快地說,
「事先就說好了裡應外合......」
「當初也沒說你要和他成親。」
「形勢所逼,假成親而已,有什麼好計較的。」
我掙開他的手,擔心他意氣用時,隨便在他的攤子上拿了樣東西,付了錢。
「你是不是喜歡上他了?」
我的動作一頓,正好此時土匪在身後喊,「弟妹,挑好了沒?」
「好了好了。」
我拿著東西匆匆走過去,心裡忽然亂成一團。
因為我發現,我竟然不想否認。
17
「怎麼了,很緊張?」
梁濟給我端來一杯茶,關心地看著我。
我對上他的視線,頓覺被火燒了一樣,匆匆挪開,將那杯茶一飲而盡。
季文牧那句話讓我發現了自己心思的一些小苗頭,且在回來的路上,這個苗頭長勢頗大,有在我的心頭安營紮寨的勢頭,氣勢洶洶讓我有些慌亂,但見到梁濟又止不住欣喜。
我只能努力克制,待到我和他的婚宴時,我蓋著蓋頭,牽著紅綢,被他引進大堂,以天地為媒,周全了夫妻之禮。
他送我回新房,挑開了紅蓋頭,在燭光搖曳之下含笑看著我,和我飲下交杯酒。
我的心跳沒有一刻是輕緩的。
湊熱鬧的人都被大當家趕了出去,留給我和他說體己話的時間。
我捏緊了拳頭,感覺蠟燭和油燈都是挨著我的臉燃燒,熱度一分不落地全部傳到了我的臉上。
分明只是一場戲,但我有些,太過入戲。
外面觥籌交錯,這裡紅燭羅帳。
但這都是假象。
我無數次這樣和自己說,終於清醒了一些。
正欲和他說話,他的食指豎在唇邊,和我指了指窗外,在我的手心裡寫,「有人在聽。」
聽?我暴露了?
他的眉眼間露出無奈之色,我忽然明白了窗外的人要聽什麼,剛剛降下溫度的臉再次蒸騰。
他坐在我身旁,低頭在我的掌心中寫字,每一筆都帶起一陣癢意,由掌心迅速蔓延到心田。
「你在這準備,我出去敬酒。」
我抓住他的手腕,有些擔心,他對我笑著,將我沒有挽起來的頭髮別到耳後,俯身過來說,
「阿珉今日格外好看。」
我看到了燭光將我和他的影子映在牆上,身影交疊,親密無間。
開門的涼風吹散了些我的燥熱,接著我便聽到屋外一陣嬉鬧聲,隨著腳步聲漸漸遠去。
我吐出一口氣,確認屋外無人,尋到靜處放,一聲炸響很快被喧囂的人聲遮蓋過去。
我送出的情報中寫了匪窩的地形,和他們說了今日成親,我會在合適的時機放出信號,讓他們進攻上來。
將信號放出去之後我就去往大堂,土匪殘暴,即使梁濟得到了他們的信任,但難保不會出現什麼意外。
我過去的時候他們都沒有起疑,反而齊齊鬨笑起來,將我推到梁濟身旁。
「你怎麼來了?」
梁濟低聲問我,有些詫異,我望過去,就望進了流光溢彩的眸子裡。
「保護我的百姓。」
他說,「有勞阿珉費心。」
他唇角含笑,舉起酒盞至我唇邊,我愣了一下,張嘴銜住杯沿,將他盞中的酒喝了小半。
「好了,去敬大當家一杯。」
他牽著我的手,在酒桌上拿起一個酒盞遞於我,倒滿了一杯。
「小弟攜內子多謝大當家成全。」
大當家一飲而盡後,其餘人紛紛過來勸酒,我看向梁濟,他沒有阻止,手中酒盞里的酒一次有一次空掉,再滿上。
他的唇也一次又一次貼上杯沿朱紅的口脂。
外面想起來兵戈相撞的聲音,有人負傷跑進來,「大當家,有官兵上山了,就要進來了。」
這裡的人立時緊張起來,拿起傢伙就要氣勢洶洶地往外走,可是沒走幾步就全都軟趴趴地倒下了。
大當家小山一樣的身軀轟然坐回主位。
我已經摸上了腰間的軟劍,準備趁其不備拿下匪首,卻對眼前眨眼間改變的局勢摸不著頭腦。
「梁濟,是你!」大當家的聲音宛如猛虎怒吼。
我看向梁濟,他輕輕將手中的酒盞放回桌面上,發出清脆的一聲響,躬身對大當家作揖。
「蒙大當家錯愛,梁濟有愧,」他站直了身體,緩緩道,「但卻無悔。」
「什麼情況?」
我問他,他轉頭面向我,指了指酒壺,說了一句廢話,「他們中藥了。」
「我也喝了......」
我突然想起了他喂我的那一口,心驟然跳快了。
「你什麼時候,怎麼不和我說?」
「並無十分把握......」
說著,他忽然臉色一變,將我拉一把了過去,抬手替我擋了一刀。
血腥味瞬間瀰漫在鼻尖,我迅速抽出軟劍,解決了那個通報的土匪,拉下他的手,血已經染透了他半截袖子,原本的紅裳此刻紅得發暗。
「沒事,尚未傷及筋骨。」
我抬頭瞪了他一眼,「你逞什麼強,我堂堂四品宣威將軍,還用得著你替我擋劍?」
「將軍不也會疼?」
半截胳膊都是血,他還能笑得出來,「將軍護百姓,我護阿珉,不是挺好?」
18
季文牧很輕易帶兵攻了上來,我只撕下來塊布,簡單的給梁濟止血,見他們來了,便想拉著梁濟去上藥。
但去路被堵上了,季文牧拉著我的胳膊,「我有話和你說。」
他的力氣太大,別說掙脫,被握著的地方都有些疼。
我回頭看向梁濟,他只是靜靜地看著我,眼中水潤的光似乎暗了下來,漸漸垂下了眼睛。
心中微疼,我脫口而出,「你等我去找你。」
接著,季文牧走得更快,我踉蹌了一會兒才跟上他的腳步。
「你幹什麼?」
握話音剛落,他就將我甩到牆邊,將我圈在牆和他之間。
極為壓迫的姿勢。
我有些不適,想要推開他,他鉗住我的手,將眉頭壓得極低,「你是不是真的喜歡上他了?」
這話說出來多不好意思。
「和你有什麼關係?」
原來我以為我和他的武力不相上下,但此刻我居然掙脫不了他,惱怒便充斥心頭,「你!」
「你不是,喜歡我的嗎?」
我一時怔住了,為他的話,也為他有些有些哽咽的聲音。
「我,握什麼時候喜歡你了?我們不是兄弟嗎?」
他忽地將我抱進懷裡,仿佛要把我牢牢地嵌進他的身體里,「你快點想起來好不好,我知道錯了,我不該過不了兄弟的檻,不該看著你受傷,我以為我們還能有很長時間,我們才是最般配的一對。我回去就和娘說,讓她給我們準備婚事。」
「你什麼毛病?」我奮力掙開他的懷抱。
他被我掙開,目光落到我身上的嫁衣,忽然動手撕下來一塊,發出刺耳的一聲響。
我捂著衣服躲開,「你瘋了!」
「我很清醒!」他停下了動作,將手中的嫁衣揉成一團,「看到你和他穿著一樣的婚服的時候,我比任何時候都清醒。」
我看著被他撕掉的地方,那裡已經露出了裡衣。
「柳珉,是你先喜歡我的,你怎麼能忘了?你怎麼能喜歡別人?」
他口口聲聲說我喜歡他,記憶化成碎片,一幕幕在我腦海中迅速拼湊出我喜歡他的十五年,連帶那股酸澀也一併湧上心頭。
我捂著心口倚靠在牆上,他的身形晃了晃,小心翼翼地問我。
「阿珉,你是不是想起來了什麼?」
我深吸了一口氣,那股難受的感覺就如過眼雲煙一樣消散了。
「季文牧,已經遲了。」
我抬眼看向他,喜歡他的十五年,我一直是堅定的喜歡,在表白之後也一直暗暗期待他能回心轉意。
可惜我等了很久,只能讓自己釋然。
「我現在只當你是兄弟了。」
12
我回去的時候,梁濟還站在原地,望向我這個方向。
他身邊人來人往,熙熙攘攘,偏偏獨他那一塊地像是被無形的屏障隔開了一樣。
「你怎麼沒去上藥?」
他受傷的胳膊現在倒是不流血了,只地面有一灘血跡。
「你不是讓我等你嗎?」
他的目光落到我破損的衣服上,「你和小季將軍,又打,切磋了?」
我搖了搖頭,「說開了一些事。」
他嗯了一聲,我帶著他去了他的房間,給他上了藥,重新包紮好,「身為大夫還不愛惜自己的身體,就該喝一個月黃連湯。」
他便笑了,我看著他笑,也沒忍住勾起嘴角。
「日後你打算去哪,還是要繼續遊歷嗎?」
我沒有勇氣坦白自己的心意,我怕我束縛了他的自由,但又實在在意,只能暗戳戳試探。
他沒有立即回答我,反而沉默下來。
「不想說也沒事。」
呆著無趣,我起身要走,他拉住我,在他身邊坐下,「還未和你說過我的身世。」
我看向他,他回望我一眼便娓娓道來。
「我所在的鎮子發生過瘟疫,我娘因此去世,我爹便成了游醫,帶著我四處治病救人,也拜訪各方名醫,為的是搜集各種疑難雜症的治癒方法,集成一本千金方,自他去世後,我便繼承了他的遺志。」
「原來是這樣。」
我的心一點點下沉,「所以千金方,還沒完成?」
「......尚未。」
我低下頭,揪著自己破爛的嫁衣,「想來這麼多年,遇到挺多困難的吧,你也是不容易。」
既然已經受了那麼多困難,那更不能讓他前功盡棄。
可我也有想守護的百姓。
我和他於雁山辭別,這一次是我先上的馬,亦不曾回頭。
回京後,凰月對剿匪大加讚賞,贊我深入虎穴,當居首功,問我有什麼想要的。
月上中天,我倒在房頂上,院子裡都是我砸下去的酒瓶,神智漸漸發昏,頭重腳輕起來。
「(「」朝臣譁然,凰月便下了調令,下朝後,季文牧擋住了我的去路,「是因為我?」
「不是。」
是我突然發現,人不能閒下來, 閒下來就會不由自主地想太多。
在邊關征戰的八年,我雖喜歡季文牧, 但我有更重要的事擔在心裡,苦悶便會少一些。
若是一直在上京呆著,在府里呆著, 看什麼,那東西的旁邊就會多出一道人影。
「在那邊呆久了,不太適應上京的生活,想回去了。」
我握拳捶向他的肩膀, 「若是得閒便去邊關找我。」
自然躲不了季伯母的一頓嘮叨, 說我就是嫌她煩, 惱她給我找婆家。
抱怨歸抱怨,但一直往我府邸跑,給我收拾的東西一樣沒少。
在我離京前日,我在東湖轉了一天, 入夜又在雲吞攤上吃了一碗雲吞。
回府的時候,燈籠底下立著一個人, 清瘦頎長。
我慢慢放慢了腳步,不確信這道人影是真的, 還是又是一道幻影。
但人影走了出來, 走到我跟前, 一雙眼睛在夜色里也水汪汪,透著亮, 勾著我的視線和心魄。
「阿珉,我想我需要你的幫忙。」
我的思維有些滯緩, 愣愣地反問,「什,什麼忙?」
「自小我運氣便好,所遇之人皆是以善相待, 所遇困難皆能逢凶化吉,最難不過兩次,擾我至今。」
他嘆息一聲,垂下眸子,「一是在城門上馬離開,二是在雁山望你離去。」
「我便想, 我見過無數疑難雜症,今日這病臨到我身, 我一人束手無策, 只能求你相助。」
我壓抑著自己的顫抖,「我又不是大夫, 不會治病。」
他低聲笑,「不需要你會治病,你本身就是千金方。」
我明了他的意思,自然是高興, 可是我很怕拘束了他。
「我要去駐守漠北, 你要是和我一起,就沒辦法遊歷了。」
他抬起手,將我攬進他的懷中,「那更好了, 我還沒去過漠北,阿珉帶我見一見。」
「你不後悔?」
「已經後悔過兩次了,此行前來便是為的今後不悔。」
(全文完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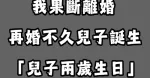
 武巧輝 • 7K次觀看
武巧輝 • 7K次觀看
 楓葉飛 • 4K次觀看
楓葉飛 • 4K次觀看














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