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些決定,就像一根針,悄無聲息地扎進你心裡,當時不覺得疼,甚至毫無感覺。
但它就在那裡,隨著時間的每一次心跳,都往深處鑽一寸。
直到半年後,當所有人都忘了那根針的存在時,它已經抵達心臟,輕輕一撥,就是一場血肉模糊的崩塌。
我老婆林靜,就是那個眼睜睜看著針扎進來,卻一言不發的人。
我當時以為她是麻木了,後來才知道,她在等,等一個親手把這根針,連本帶利還回去的機會。

01
"爸,這房子……真的賣了?"
飯桌上,林靜的聲音很輕,像一片羽毛,飄落在滾燙的油鍋里,連個聲響都沒有,就被灼人的氣氛吞沒了。
我坐在她旁邊,緊緊攥著她的手,能感覺到她掌心裡一片冰涼的冷汗。
坐在主位上的岳父,陳建國,今年剛滿七十,精神頭卻遠勝過同齡人。
他今天特意穿了件嶄新的深紅色唐裝,滿面紅光,仿佛不是在宣布一個足以顛覆我們家庭的決定,而是在主持一場盛大的慶功宴。
他端起酒杯,對滿滿一桌子菜視而不見,目光越過林靜,精準地落在了他寶貝兒子,也就是我小舅子陳凱的臉上。
"賣了!260萬,一分不少!"岳父的聲音洪亮,帶著不容置疑的威嚴和一絲炫耀,"錢,我已經全部轉給陳凱了。他下個月就要結婚,婚房、車子、彩禮,哪樣不要錢?作為家裡唯一的男人,我必須為他鋪好路!"
"唯一的男人"這五個字,像一把淬了毒的錐子,狠狠刺入我的耳膜。
我猛地抬頭,死死盯住岳父那張得意的臉。
我和林靜結婚八年,我自問對二老孝順有加,逢年過節的禮品,日常的噓寒問暖,生病時的陪護,我哪一樣做得比陳凱差?
可到頭來,在這個家裡,我依然是個外人,甚至連林靜,他唯一的女兒,都成了潑出去的水。
我身邊的林靜,肩膀微微顫抖了一下,然後就再無動靜。
她低著頭,長長的睫毛垂下,在眼瞼處投下一片灰暗的影。
我看不清她的表情,只能看到她放在桌下的另一隻手,指甲深深地陷進了掌心。
我的火氣"噌"地一下就頂到了天靈蓋。
"爸,您這話是什麼意思?"我儘量壓抑著怒火,但聲音還是忍不住發抖,"這房子是您和媽的婚房,裡面也有林靜從小到大的回憶。賣掉我們沒意見,畢竟是您的財產,您有權處置。但是260萬,一分都不給林靜留?您這也太偏心了吧!"
岳母在一旁尷尬地搓著手,不停地給我使眼色,嘴裡打著圓場:"哎呀,張偉,你少說兩句。你爸這麼做,也是為了這個家好。你妹妹以後還不得靠著她弟弟?"
"為了這個家好?"我氣得發笑,"哪個家?陳凱的家嗎?林靜就不是您的女兒了?她結婚的時候,您給了什麼?一套用了十幾年的舊家電,還有兩床棉被!現在陳凱結婚,您直接把老底都掏空了,260萬啊!那不是26萬!"
對面的陳凱,正低頭玩著手機,聽到我的話,他懶洋洋地抬起眼皮,嘴角一撇,露出一抹譏諷的笑:"姐夫,你這麼激動幹什麼?我爸媽的錢,願意給誰就給誰。再說了,我姐都嫁給你了,是你們張家的人了,管我們陳家的事幹嘛?難不成,你還惦記著我爸這點家產?"
這番話,無恥到了極點。
我氣得渾身發抖,剛要站起來理論,卻被林靜一把死死按住。
我扭頭看她,她依然低著頭,只是緩緩地搖了搖。
那動作很輕,卻帶著一種不容反抗的力量。
岳父陳建國把酒杯重重地往桌上一放,發出"砰"的一聲巨響。
"張偉,我告訴你!"他指著我的鼻子,唾沫星子橫飛,"我陳家的事,還輪不到你一個外人來指手畫腳!我兒子是根,是傳宗接代的!女兒是什麼?女兒遲早是別人家的!我把錢給他,天經地義!林靜要是懂事,就該為她弟弟高興!"
他頓了頓,似乎覺得話說得太重,又緩和了語氣,但那份高高在上的施捨意味卻更濃了。
"再說了,你們倆日子不是過得挺好嗎?都有房有車的,也不缺這點錢。陳凱不一樣,他剛起步,我這個當爹的,不拉他一把誰拉他?手心手背都是肉,我能不疼林靜嗎?但凡事總有個輕重緩急。等以後陳凱出息了,還能虧待了你們?"
這番話,聽得我胃裡一陣翻江倒海。
什麼叫輕重緩急?
難道女兒的幸福和尊嚴,就永遠排在兒子後面?
我看著林靜,心疼得無以復加。
從始至終,她就像一個局外人,沉默地坐著,仿佛這場關於260萬歸屬的家庭戰爭,與她毫無關係。
我知道,她的心,一定比我更痛。
那頓飯,最終不歡而散。
回去的路上,我開著車,胸口堵得像壓了一塊巨石。
我幾次想開口,想問問林靜為什麼這麼能忍,為什麼不為自己爭一句。
可當我從後視鏡里看到她的臉時,所有的話都咽了回去。
她靠在車窗上,靜靜地看著窗外飛速倒退的街景,路燈的光一閃一閃地掠過她的臉,明暗交替。
她的臉上沒有憤怒,沒有悲傷,甚至沒有一絲波瀾。
那是一種……死寂般的平靜。
我從未見過她這個樣子,那平靜之下,仿佛壓抑著一座即將噴發的火山。
我突然有些害怕。
我寧願她大哭大鬧一場,也比現在這副模樣要好。
回到家,我終於忍不住了。
"靜靜,你到底怎麼想的?那是260萬!不是260塊!爸這麼做,你真的一點都不在乎嗎?"
林靜沒有看我,她換了鞋,走進客廳,給自己倒了一杯水,然後才慢慢轉過身。
"在乎。"她輕輕地說出兩個字,聲音平靜得像一潭深水,"我在乎得要命。"
"那……"
她打斷我,目光第一次直視我的眼睛,那眼神深邃得讓我心驚。
"張偉,"她說,"你信我嗎?"
我愣住了。
"這口氣,我咽不下。但現在不是爭的時候。"她一字一頓,聲音不大,卻擲地有聲,"你什麼都別做,什麼都別說。我們,等著。"
"等?等什麼?"
"等一個,讓他們把吃下去的東西,親口吐出來的機會。"
02
林靜的話,像一顆定心丸,暫時穩住了我即將爆發的情緒。
但我心裡依然憋著一股邪火,燒得我五臟六腑都疼。
我無法理解,面對如此赤裸裸的不公和羞辱,她為何能保持那種近乎冷酷的理智。
夜裡,我翻來覆去睡不著。
林靜躺在我身邊,呼吸均勻,似乎早已進入了夢鄉。
可我知道,她和我一樣,醒著。
"你是不是早就料到會這樣?"我睜著眼睛,對著天花板輕聲問道。
身邊的人沉默了片刻,然後傳來一聲幾不可聞的嘆息。
"張偉,你還記得我們結婚前,我爸找你談話嗎?"
我怎麼會不記得。
那是一個夏天的午後,岳父把我約到一家茶館,開門見山地告訴我,林靜從小被他們寵壞了,沒什麼心眼,讓我以後多擔待。
他說,家裡沒什麼錢,給不了林靜豐厚的嫁妝,希望我不要嫌棄。
他還說,以後陳凱就是我的親弟弟,要我多幫襯著他。
當時我年輕,滿心滿眼都是對林靜的愛,覺得岳父樸實真誠,說得都是實在話。
我拍著胸脯向他保證,一定會對林靜好,會把他的話當成聖旨。
現在想來,那哪裡是談話,分明是一場精心設計的"免責聲明"。
他把他作為父親的所有責任,輕飄飄地,全部轉移到了我的身上。
"他那時候就在為今天鋪路了。"林靜的聲音在黑暗中顯得格外清晰,"從我記事起,他眼裡就只有陳凱。家裡只有一個雞蛋,一定是煮給陳凱吃;買了一件新衣服,一定是陳凱先挑。我考上大學那年,他擺了三桌酒,陳凱初中畢業去讀技校,他擺了十桌。"
這些往事,林靜很少提起。
我只知道岳父偏心,卻不知道已經到了這種令人髮指的地步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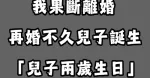
 武巧輝 • 6K次觀看
武巧輝 • 6K次觀看
 楓葉飛 • 4K次觀看
楓葉飛 • 4K次觀看














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