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們都以為我是任人宰割的羔羊,溫順,卑微,連反抗的尖叫都發不出來。
當婆婆張翠芬將她啃得精光的骨頭輕蔑地丟進我碗里時,我甚至會微笑著對她說謝謝。
我的丈夫顧言心疼地攥緊拳頭,小姑子顧莉滿眼鄙夷,而我,只是平靜地,一口一口,將那份混著殘渣的羞辱咽下。
他們不知道,每一次低頭,每一次順從,都是在為最終的爆發積蓄力量。
在那張看似尋常的餐桌布下,藏著我們這個家最大的秘密,一份價值三百萬的財產贈與協議,那是我的丈夫,用他全部的私產,為我鋪就的逃生之路。
而我,早已磨利了爪牙,只等掀桌的那一刻。

01
晚飯的氛圍一如既往的壓抑。
紅木圓桌上擺著四菜一湯,精緻得如同酒店的樣品,卻透著一股冰冷。
我,林晚,安靜地坐在屬於我的位置上,小口地扒拉著碗里的白米飯,努力將自己的存在感降到最低。
坐在主位上的婆婆張翠芬,正慢條斯理地用濕巾擦著手,她剛吃完一塊最愛的糖醋排骨,嘴角還帶著一絲油亮的滿足。
她眼角的餘光掃過我,那眼神像是在打量一件不甚滿意的家具。
「小晚啊,」她開了口,聲音不大,卻像一根針,精準地刺破了餐桌上虛假的寧靜,「你看你,光吃白飯怎麼行,一點營養都沒有。女孩子家家的,太瘦了不好生養。」
我的心猛地一沉,知道「好戲」要上演了。
坐在我身旁的丈夫顧言立刻緊張起來,他放在桌下的手悄悄伸過來,握住了我的手,掌心一片濡濕的汗意。
我能感覺到他肌肉的緊繃,像一張即將拉滿的弓。
我反手輕輕拍了拍他的手背,示意他冷靜。
對面的小姑子顧莉「噗嗤」一聲笑了出來,她放下筷子,一副看好戲的模樣:「媽,你就是太心疼嫂子了。嫂子從鄉下來的,可能沒吃過什麼好東西,你得多『照顧照顧』她。」
「照顧」兩個字,她咬得特別重,充滿了不加掩飾的嘲諷。
張翠芬仿佛被女兒的話取悅了,她點了點頭,然後做出了那個已經重複了無數次的動作——她將自己盤子裡啃得乾乾淨淨、只剩下一層唾液薄膜的排骨骨頭,用筷子夾起來,「啪」的一聲,丟進了我的碗里。
骨頭落在米飯上,發出沉悶的聲響,幾粒米飯被濺到了我的臉上。
整個世界仿佛在那一刻按下了靜音鍵。
我能清晰地聽到顧言倒吸一口涼氣的聲音,和他牙齒咬合時發出的「咯咯」聲。
我甚至能感覺到他全身的怒火已經衝到了臨界點,下一秒就要爆發。
「媽!你幹什麼!」他終於忍不住低吼了出來。
「我幹什麼?我疼你媳婦啊!」張翠芬立刻把臉一板,聲音陡然拔高了八度,「你看看這骨頭上,還有這麼多肉呢,扔了多可惜?我們那個年代,想吃這個都吃不上!讓她吃是福氣,你吼什麼吼?真是娶了媳婦忘了娘,一點家教都沒有!」
一頂「沒有家教」的大帽子扣下來,顧言的臉瞬間漲成了豬肝色。
他想反駁,卻被母親蠻不講理的氣勢堵得說不出話來。
這就是我們家的常態。
張翠芬在這個家裡,就是絕對的獨裁者。
顧莉在一旁煽風點火:「就是啊哥,媽也是為了嫂子好,你那麼激動幹嘛?你看嫂子自己都沒說什麼呢。」
所有人的目光,瞬間都聚焦在了我的臉上。
有婆婆的輕蔑,有小姑子的譏諷,還有顧言那混雜著憤怒、心疼和無力的複雜眼神。
我沉默了片刻,然後,緩緩地抬起頭,臉上綻開一個微笑。
那是一個極其溫順,甚至帶著一絲感激的笑容。
「謝謝媽,」我的聲音很輕,卻很清晰,「媽說得對,不能浪費糧食。」
說完,在他們錯愕的注視下,我拿起筷子,夾起了那根屈辱的骨頭,放進嘴裡,仔細地、認真地,將上面殘留的最後一絲肉末和醬汁都吮吸乾淨。
然後,我將那根被我吮吸得比張翠芬啃得還乾淨的骨頭,輕輕放在了桌邊的空碟子裡。
做完這一切,我繼續低下頭,扒拉著碗里那被骨頭玷污過的米飯,仿佛剛才什麼都沒有發生。
餐桌上的氣氛變得更加詭異。
張翠芬和顧莉的臉上,得意的笑容僵住了,取而代之的是一絲困惑和不解。
她們大概以為我會哭,會鬧,會像顧言一樣爆發。
她們準備好了一百句刻薄的話來回擊我,卻沒想到,我竟然如此平靜地接受了。
就像一拳打在了棉花上,讓她們覺得索然無味,甚至還有一絲說不清道不明的詭異。
只有顧言,他眼中的怒火漸漸熄滅,轉而被一種更深沉的痛楚所取代。
他知道,我不是沒有感覺,我只是在忍。
一頓飯在死寂中結束。
我像往常一樣收拾碗筷,走進廚房。
顧言跟了進來,從背後抱住我,把頭埋在我的頸窩裡,聲音沙啞得厲害:「對不起,晚晚……對不起……」
我關上水龍頭,轉過身,用手指輕輕撫平他緊蹙的眉頭:「沒關係,我習慣了。」
「可我不習慣!我受不了她們這樣對你!」他低吼著,像一頭被困住的野獸,「我們離婚吧,晚晚!你離開這個家,我不想你再受這種委屈!」
「離婚?」我笑了,笑得有些蒼涼,「離婚,然後呢?我凈身出戶,回到那個我好不容易才逃離的小地方,繼續過以前的日子?顧言,我們結婚的時候,你答應過我,會給我一個家的。」
「可這不是家!這是地獄!」
「是,」我點了點頭,直視著他的眼睛,「所以,我們要做的不是讓我一個人逃離,而是我們一起。你忘了嗎?我們的計劃。」
提到「計劃」兩個字,顧言的身體瞬間僵住。
我伸出手,輕輕撫摸著餐廳那張紅木圓桌的邊緣,指尖划過華麗的刺繡桌布。
那冰涼絲滑的觸感,像是在提醒我什麼。
「就快了,」我的聲音輕得像一陣風,「再忍一忍,一切就都結束了。她們現在給我的每一次羞辱,將來,都會成為我們自由的墊腳石。」
我的目光穿過廚房的門,落在客廳里正在看電視的張翠芬和顧莉身上。
她們笑得前仰後合,完全沒有注意到,廚房裡這對看似絕望的夫妻,正在謀划著一場足以顛覆整個家庭的驚天海嘯。
而那份被我小心藏在桌布夾層里的,由顧言親筆簽下的三百萬財產贈與協議,就是我們引爆這場海嘯的唯一武器。
02
這個計劃,並非我處心積慮的設計,而是被逼到絕境後的唯一生路。
我和顧言是大學同學,我們的愛情始於圖書館裡一次偶然的邂逅,乾淨純粹,不摻雜任何雜質。
畢業後,顧言向我求婚,我帶著對未來的無限憧憬,嫁給了他。
那時我天真地以為,只要有愛,就可以克服一切。
可我錯了。
我錯估了「門當戶對」這四個字在中國式婚姻里的分量。
顧家在本地是小有名氣的富裕家庭,經營著一家不大不小的公司。
而我,出身於一個偏遠小鎮的普通工薪家庭。
在張翠芬眼裡,我嫁給顧言,就是「麻雀飛上枝頭變鳳凰」,是圖他們家的錢。
所以從我踏進這個家門的第一天起,羞辱和刁難就成了家常便飯。
她嫌棄我帶來的嫁妝寒酸,當著親戚的面把我的箱子翻了個底朝天,一件件點評,說我的衣服料子像抹布。
她嫌棄我不會做家務,明明家裡有保姆,卻偏要指使我跪在地上用毛巾擦幾百平的木地板。
她甚至會監視我給我父母打電話,聽到我問候家人,就會在一旁陰陽怪氣地說:「真是個填不滿的無底洞,嫁出去了還老惦記著娘家。」
起初,我嘗試反抗。
我會和她爭辯,告訴她人人平等,告訴她我的父母把我養大不容易。
但每一次反抗,換來的都是更猛烈的暴風雨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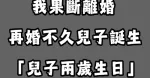
 武巧輝 • 6K次觀看
武巧輝 • 6K次觀看
 楓葉飛 • 4K次觀看
楓葉飛 • 4K次觀看














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