張翠芬會一哭二鬧三上吊,指著顧言的鼻子罵他娶了媳婦忘了娘的白眼狼。
而顧言,他雖然愛我,但在強勢了一輩子的母親面前,卻總是顯得那麼蒼白無力。
他的每一次維護,最後都會以他的道歉和我的妥協告終。
在這個家裡,張翠芬牢牢掌控著經濟大權,顧言雖然在公司掛著副總的頭銜,但每月的零花錢都需要張翠芬審批。
他就像一隻被剪了翅膀的鳥,空有飛翔的慾望,卻沒有掙脫牢籠的能力。
我漸漸地,心冷了,絕望了。
轉機發生在一個雨夜,半年前。
那天因為我給家裡寄了五百塊錢,被張翠芬發現後,她爆發了有史以來最激烈的一次爭吵。
她把我的東西扔了一地,指著我的鼻子罵我是「扶弟魔」、「吸血鬼」,罵我全家都是想攀附他們家的窮光蛋。
最讓我崩潰的是,她翻出了我母親在我結婚時送我的一支銀手鐲,那是我外婆傳下來的唯一念想。
她拿著那支已經有些發黑的手鐲,滿臉鄙夷地說:「就這種破爛玩意兒也好意思拿出手?不知道的還以為是哪個地攤上十塊錢買的。」
說完,她隨手就把手鐲扔出了窗外。
那一刻,我所有的理智都崩塌了。
我尖叫著衝過去,和她廝打在一起。
那是我第一次,也是唯一一次和她動手。
結果可想而知。
我被她撓得滿臉是血,最後被她和顧莉聯手鎖進了房間。
顧言回來時,看到的就是蜷縮在角落,渾身是傷,狼狽不堪的我。
他抱著我,一個一米八幾的大男人,哭得像個孩子。
「對不起,晚晚,都是我沒用,是我沒保護好你……」他一遍遍地重複著。
那天晚上,我們聊了很久。
我第一次向他提出了離婚。
我告訴他,我真的撐不下去了。
他抱著我,沉默了許久,然後,他抬起頭,眼睛裡閃爍著一種我從未見過的、破釜沉舟的光芒。
「晚晚,別走,」他啞著嗓子說,「再給我一次機會,給我……也給你自己一次機會。」
他告訴我一個秘密。
一個連張翠芬都不知道的秘密。
顧言的外公,在他上大學的時候,就預見到了女兒的強勢性格可能會給未來外孫的婚姻帶來不幸。
所以,他私下裡以信託基金的方式,給顧言留下了一筆遺產。
這筆錢,只有在顧言年滿三十歲或者結婚後,才能由他自己全權支配。
這筆錢,不多不少,正好三百萬。
「我媽一直想讓我娶一個對家族生意有幫助的富家女,所以我一直沒敢動這筆錢,我怕她知道了,會想方設法奪走,」顧言的眼睛在黑暗中亮得驚人,「但現在,我不想再忍了。晚晚,這筆錢,我全部給你。」
我愣住了。
「我們簽一份財產贈與協議,」他抓著我的手,語氣急切而堅定,「我把這三百萬,以及這套房子的產權——這房子是我爸婚前買給我的,也在我個人名下——全部無償贈與給你。然後,你再和我離婚。這樣,你就可以帶著這些錢,徹底離開這裡,開始新的生活。遠遠地離開,去一個她們永遠找不到你的地方,過你想要的日子。」
我看著他,心臟狂跳。
我從他的眼睛裡,看到了絕望,也看到了最深沉的愛。
他寧願散盡家財,也要換我自由。
「那你呢?」我顫聲問。
「我?」他苦笑了一下,「我就留在這裡,繼續當我的傀儡兒子。只要你安全了,自由了,我就放心了。」
那一刻,我的眼淚洶湧而出。
我不是因為那三百萬,而是因為眼前這個男人,在最絕望的境地里,為我撕開了一道光。
但是,我拒絕了。
「不,」我擦乾眼淚,搖了搖頭,「我不要一個人走。要走,我們一起走。」
一個全新的,更大膽的計劃,在我腦中迅速成形。
「顧言,這份協議,我們簽。但這三百萬,不是我的分手費,而是我們新生活的啟動資金。從今天起,我要忍,我要演。我要讓張翠芬以為她已經徹底把我踩在了腳下,讓她放鬆警惕。而你,要做的就是配合我,同時,悄悄地把所有的手續辦好。」
「我要讓她在最得意,最以為自己掌控一切的時候,親眼看著她最看不起的兒媳婦,帶走她最引以為傲的兒子,和一大筆她聞所未聞的財富。」
「我要的不是逃離,是復仇。」
顧言被我的話驚得目瞪口呆,但很快,他的眼中也燃起了復仇的火焰。
於是,在那天深夜,我們避開家裡所有的監控,在書房裡,一筆一划地簽下了那份足以改變我們命運的《財產贈與協議》。
為了安全,我沒有把協議放在任何可能被發現的地方,而是利用我唯一能掌控的「領地」——那張每天都在上演羞辱大戲的餐桌。
我小心翼翼地將摺疊好的協議,塞進了桌布華麗刺繡的夾層里。
最危險的地方,就是最安全的地方。
從那天起,我變了。
我收起了所有的鋒芒,變成了一個逆來順受、唯唯諾諾的「完美兒媳」。
而扔骨頭,就是從那之後開始的。
第一次,張翠芬試探性地把骨頭扔進我碗里時,我按照計劃,微笑著吃了。
她得到了巨大的滿足感和掌控感。
從此,這便成了她向我宣示主權的保留節目。
她不知道,她每一次高高在上的「賞賜」,都像一把錘子,狠狠地砸在顧言的心上,讓他辦理財產轉移手續的決心,更加堅定一分。
而我每一次的低頭和微笑,都是在心裡默念:
快了,就快了。
03

自從我開啟「溫順羔羊」模式後,張翠芬和顧莉對我的「欺凌」也隨之升級,變得更加肆無忌憚和富有創意。
扔骨頭只是開胃小菜,她們真正的「樂趣」在於精神上的全面碾壓。
比如,家裡來了客人,張翠芬會特意把我叫到客廳,當著所有人的面,笑盈盈地說:「這是我兒媳婦林晚,沒什麼大本事,就是手腳還算麻利。來,小晚,去給王阿姨她們切一盤水果,記得要雕花啊,你在老家不是最擅長干這些手工活嗎?」
她故意模糊了「心靈手巧」和「下人幹活」的界限,用最溫柔的語氣,說著最傷人的話。
那些貴婦人們便會用一種審視的、帶著憐憫的目光看著我,仿佛在看一個被買回來的廉價商品。
而我,只能微笑著點頭,走進廚房,用那雙曾經拿過設計獎的手,笨拙地學著網上搜來的教程,給蘋果雕花,給橙子刻兔子。
顧莉則更喜歡在細節上折磨我。
她會故意把剛塗了昂貴指甲油的手伸到我面前,命令我給她繫鞋帶,理由是「怕刮花了新做的指甲」。
她會在我剛拖乾淨的地板上,踩上幾個清晰的腳印,然後皺著眉說:「嫂子,你怎麼回事,地都拖不幹凈。」
最過分的一次,是她養的那隻名叫「公主」的波斯貓。
那天,顧莉抱著貓,斜睨著正在陽台晾衣服的我,懶洋洋地說:「嫂子,『公主』的貓砂盆該換了,你去處理一下吧。」
我點頭說好。
「等一下,」她叫住我,「今天『公主』好像有點便秘,你清理的時候,順便看看它拉的粑粑形態正不正常,最好拍個照,我發給寵物醫生問問。」
那一瞬間,我攥著衣架的手指因為用力而陣陣發白。
讓我去鏟貓屎,還要我觀察、拍照。
這已經不是羞辱,而是赤裸裸地將我的尊嚴放在地上踐踏。
廚房裡的保姆都露出了不忍的表情。
我深吸了一口氣,將那股幾乎要噴涌而出的怒火強行壓了下去。
我對自己說:林晚,冷靜,想想那份協議,想想你和顧言的未來。
這都是暫時的。
我轉過身,臉上再次掛上了那副標準得像面具一樣的微笑:「好的,小莉。我這就去。」
我走進那個放著貓砂盆的小房間,刺鼻的臭味撲面而來。
我忍著噁心,戴上手套,拿出手機,對著那盆污穢之物,拍下了一張清晰的照片。
發給顧莉後,我聽到了客廳里她和張翠芬爆發出的、毫不掩飾的嘲笑聲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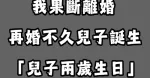
 武巧輝 • 6K次觀看
武巧輝 • 6K次觀看
 楓葉飛 • 4K次觀看
楓葉飛 • 4K次觀看














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