「媽,你看她,真的拍了!哈哈哈,真是個蠢貨,讓她幹什麼就幹什麼!」
「跟條狗似的,聽話就行。」張翠芬的聲音里充滿了得意。
那一刻,我站在原地,眼淚在眼眶裡打轉,卻倔強地不讓它掉下來。
我抬起頭,看著窗外灰濛濛的天空,心裡一遍又一遍地重複著:
「值得的,這一切都是值得的。」
顧言回家後,顧莉添油加醋地把這件事當成笑話講給他聽。
我看到顧言的臉色瞬間變得鐵青,他放在身側的拳頭捏得咯咯作響。
他猛地站起來,似乎想說什麼,卻被我用眼神制止了。
晚上回到房間,他再也忍不住了,一拳狠狠地砸在牆上。
「她們太過分了!晚晚,她們根本沒把你當人看!」他雙眼通紅,聲音里充滿了痛苦和自責。
我從背後輕輕抱住他,把臉貼在他寬闊的背上:「我沒事,顧言。真的。」
「怎麼可能沒事!」他轉過身,捧著我的臉,眼中的心疼幾乎要溢出來,「我看到顧莉手機里的那張照片了……我……我真想殺了他們!」
「別說傻話,」我踮起腳,吻了吻他的額頭,「你越是這樣,我越覺得我們做的是對的。她們越是瘋狂,就越證明她們的內心是多麼的空虛和惡毒。顧言,你聽我說,你現在最重要的任務,不是和她們吵架,而是儘快把最後的手續跑完。你知道嗎,今天她們讓我拍那張照片的時候,我一點也不覺得難過。」
他疑惑地看著我。
我笑了,那是在他面前,我才會露出的、帶著一絲狡黠的真實的笑。
「我只覺得,我手裡又多了一份證據。一份能證明你母親和你妹妹是如何精神虐待我的證據。將來如果真的鬧上法庭,這些都會是她們應得的報應。」
是的,我沒有撒謊。
從那次被扔銀手鐲之後,我就學會了留存證據。
每一次張翠芬和顧莉的刁難,每一次她們的冷嘲熱諷,我都會用一支藏在口袋裡的錄音筆,悄悄錄下來。
那些她們自以為是的「家規」,那些她們脫口而出的侮辱性詞彙,都成了我資料庫里冰冷的音頻文件。
包括今天,顧莉讓我拍貓屎的那段對話,也被我完整地錄了下來。
顧言愣愣地看著我,仿佛第一次認識我一般。
他眼中的我,不再是那個只會哭泣和忍耐的柔弱女孩,而是一個冷靜、理智,甚至帶著幾分冷酷的復仇女神。
「晚晚,你……」
「我只是在保護我們自己,」我打斷他,眼神堅定,「我們不能只指望那份協議。我們要做好萬全的準備。顧言,答應我,加快速度,我怕我……快要演不下去了。」
我的聲音裡帶上了一絲不易察ác的顫抖。
他緊緊地把我擁入懷中,下巴抵在我的頭頂,聲音沉重而決絕:
「我知道了。最後一步,房產過戶,我已經約好律師了。就在下周三。晚晚,再堅持一個星期。就一個星期。」
一個星期。
我在心裡默念著這個時間。
七天,一百六十八個小時。
就像一場漫長的馬拉松,我已經能看到終點線的旗幟在向我招手。
只要我能撐過這最後的七天。
04
距離約定的過戶日期越來越近,我的內心既期盼又緊張,而張翠芬的疑心,也像藤蔓一樣,開始瘋狂滋長。
正如我所預料的,一個被長期壓迫的人突然變得「逆來順受」,這本身就是一種不合常理的現象。
我的平靜,在張翠芬眼裡,漸漸從「愚蠢聽話」變成了「高深莫測」。
她開始不動聲色地觀察我。
我接電話時,她會狀似無意地從我身邊經過,豎起耳朵聽。
我回房間,她會找藉口進來,看看我是在看書還是在玩手機。
甚至連我扔掉的垃圾,她都會讓保姆檢查一遍,看看有沒有什麼「可疑」的購物小票。
她的試探也變得更加陰險。
一天下午,我正在客廳看書,她端著一碗剛燉好的燕窩走過來,臉上帶著罕見的慈祥笑容。
「小晚,來,累了吧?喝碗燕窩補補身體。」
我受寵若驚地接過,說了聲「謝謝媽」。
就在我準備喝的時候,她看似無意地提起:「對了,前幾天我跟你王阿姨她們打麻將,聽她說她兒媳婦最近不太安分,好像在外面有人了,正琢磨著怎麼把她凈身出戶呢。你說現在這小姑娘啊,心思真是越來越多了。」
她的眼睛像鷹一樣,死死地盯著我的臉,不放過任何一絲表情變化。
我心裡一凜,知道這是在敲山震虎,試探我是否也有「二心」。
我放下碗,抬起頭,臉上露出恰到好處的困惑和天真:「啊?王阿姨的兒媳婦怎麼會這樣啊?她老公對她不是挺好的嗎?真是不懂珍惜。」
然後,我像是想到了什麼,一臉認真地看著張翠芬,補充道:「媽,你放心,我跟顧言感情好著呢,我這輩子都不會做對不起他的事。再說了,我們家顧言這麼優秀,我怎麼可能看得上外面的男人。」
我的語氣真誠無比,眼神清澈見底,一番話既表明了「忠心」,又不動聲色地捧了顧言和她一下。
張翠芬審視了我半天,似乎沒找出什麼破綻,只好悻悻地「嗯」了一聲,讓我快點趁熱喝。
我端起碗,用勺子輕輕攪動著碗里晶瑩的燕窩,心中冷笑。
她以為她是在釣魚,卻不知道,我這條魚,早就看穿了她所有的魚餌。
然而,真正的危機,發生在周二的晚上,也就是過戶的前一天。
那天晚飯,氣氛格外凝重。
張翠fen一言不發,只是用那雙精明的眼睛,在我跟顧言之間來回掃視。
顧言因為第二天就要辦成「大事」,神情中難免帶了一絲不易察覺的激動和緊張,這絲情緒顯然被張翠芬捕捉到了。
晚飯後,張翠芬突然叫住了正要回房的顧言。
「阿言,你跟我到書房來一下,我有點事問你。」她的語氣不容置喙。
我心裡「咯噔」一下。
顧言給了我一個「放心」的眼神,跟著張翠芬進了書房。
我站在門外,心提到了嗓子眼。
書房的隔音很好,我什麼也聽不見。
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,每一秒都像一個世紀那麼漫長。
大約過了半個小時,書房的門開了。
顧言走了出來,臉色有些蒼白,但神情還算鎮定。
張翠芬跟在他身後,臉色陰沉得能滴出水來。
她沒有看我,徑直回了自己的房間,「砰」地一聲關上了門。
我趕緊拉著顧言回到我們自己的房間,關上門,急切地問:「她跟你說什麼了?她是不是發現了什麼?」
顧言深吸一口氣,努力讓自己平靜下來。
「她問我,最近是不是有什麼事瞞著她。」他低聲說,「她覺得我跟以前不一樣了,還問我是不是在外面做了什麼投資,虧了錢不敢告訴她。」
「你怎麼回答的?」我緊張地追問。
「我按照我們之前商量好的說辭,說公司最近有個項目壓力比較大,所以心情不太好。」顧言頓了頓,臉色更加難看,「但是……她不信。」
「她說,她感覺我要『飛』了,要脫離她的掌控了。
她還說,如果我敢有什麼歪心思,她絕對不會放過『那個攛掇我的狐狸精』。」
他口中的「狐狸精」,指的自然是我。
我的心徹底沉了下去。
張翠芬的直覺,遠比我們想像的要敏銳。
她雖然沒有證據,但已經嗅到了危險的氣息。
「最糟糕的是,」顧言的聲音裡帶著一絲顫抖,「她說明天她要去公司查帳,還要把公司財務的U盾和印章全部收回到她自己手裡。」
這個消息如同一道晴天霹靂!
顧言雖然是副總,但公司的財務一直由張翠芬親手把控。
她這麼做,等於是在徹底架空顧言,斷絕他任何動用大額資金的可能。
雖然我們轉移的三百萬是顧言的私人信託財產,與公司無關,但她這一手,無疑是給我們敲響了最響亮的警鐘。
她已經開始行動了。
「那……那我們明天還去過戶嗎?」我慌了,第一次感到了真正的恐慌。
如果明天過戶的時候,被她發現,前功盡棄不說,我和顧言將要面對的,是她雷霆萬鈞的報復。
到那時,我們連一絲一毫的反抗餘地都沒有。
顧言沉默了。
房間裡死一般的寂靜,我甚至能聽到自己劇烈的心跳聲。
許久,他抬起頭,眼中閃過一絲決絕的狠厲。
「去!必須去!」他一字一頓地說,「箭在弦上,不得不發!她越是這樣,越說明我們必須馬上走!明天就是我們最後的機會!晚晚,成敗在此一舉。不管明天發生什麼,我們都要賭一把!」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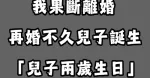
 武巧輝 • 7K次觀看
武巧輝 • 7K次觀看
 楓葉飛 • 4K次觀看
楓葉飛 • 4K次觀看














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