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看著他堅定的眼神,那顆慌亂的心,也慢慢地鎮定了下來。
是啊,我們已經沒有退路了。
要麼,在沉默中被徹底吞噬。
要麼,在爆發中獲得新生。
我重重地點了點頭:「好,賭一把!」
那個晚上,我們誰都沒有睡。
我們睜著眼睛,看著窗外的天色一點點由黑變白,像兩個即將走上刑場的囚犯,等待著黎明的審判。
我們都不知道,等待我們的,將是一場比想像中更加猛烈、更加猝不及t防的狂風暴雨。
05
周三,決戰之日。
我和顧言強作鎮定地和張翠芬、顧莉一起吃早餐。
空氣里的火藥味濃得幾乎要爆炸。
張翠芬一言不發,只是用審視的目光死死地盯著我們,仿佛要將我們看穿。
顧言找了個藉口,說公司有急事,需要提前出門。
我也說要去超市買些東西。
我們約定好十點在房產交易中心門口見面。
我能感覺到張翠fen的目光像芒刺一樣扎在我的背上。
出門後,我繞了幾個圈,確定沒人跟蹤,才坐上了去交易中心的地鐵。
一路上,我的心跳得飛快,手心裡全是冷汗。
我一遍遍地在心裡祈禱,一切順利,一切順利。
然而,命運似乎偏要跟我們開一個天大的玩笑。
九點五十,我剛走出地鐵口,就接到了顧言的電話,他的聲音充滿了前所未有的驚惶和急切:「晚晚!快!計劃有變!我媽不知道怎麼回事,提前去了公司,堵住了我!她現在正帶著我往家裡趕,說要開家庭會議!你千萬不要去交易中心了,趕緊回家!快!」
「什麼?!」我大腦「嗡」的一聲,一片空白。
她怎麼會……她怎麼會堵住顧言的?
「我不知道!她可能在我車上裝了定位器!我來不及解釋了,你快回來,不然我們兩個人都走不掉!」顧言的聲音裡帶著哭腔。
電話被掛斷了。
我站在人來人往的街頭,渾身冰冷,手腳都在發抖。
失敗了。
在我們離成功只有一步之遙的時候,徹底失敗了。
我失魂落魄地回到那個名為「家」的牢籠。
一進門,就看到客廳里三堂會審的架勢。
張翠芬坐在主位的沙發上,臉色鐵青。
顧莉站在她身後,一臉幸災樂禍。
顧言則垂著頭,像個做錯事的孩子,站在一旁。
看到我進來,張翠芬冷笑一聲:「喲,我們家的大忙人回來了?怎麼,超市逛完了?」
我沒有說話,只是走到顧言身邊,和他並排站在一起。
「說吧,」張翠芬猛地一拍茶几,上面的茶杯被震得跳了起來,「你們兩個,今天到底想幹什麼去?別跟我說是去公司,去超市!顧言的車,直接開到了房產交易中心附近!當我老糊塗了嗎?!」
原來是車載GPS。
我們千算萬算,竟然漏掉了這個最簡單的東西。
顧言嘴唇動了動,想說什麼,卻被張翠fen凌厲的眼神堵了回去。
「你們不說是吧?好!」張翠芬站起身,眼神狠厲地在我和顧言身上掃過,「我本來還想給你們留點面子,既然你們敬酒不吃吃罰酒,那就別怪我了!」
她轉身對顧莉說:「小莉,去!把他們房間給我仔仔細細地搜一遍!我就不信,找不出一點狐狸尾巴來!」
顧莉早就等不及了,應了一聲,立刻像一隻興奮的獵犬,帶著保姆衝進了我們的房間。
我跟顧言的心,瞬間沉到了谷底。
完了。
錄音筆,還有一些我們準備帶走的資料,都還在房間裡。
雖然協議本體藏在桌布下,但那些東西一旦被搜出來,也足以定我們的罪了。
房間裡傳來一陣翻箱倒櫃的聲音,噼里啪啦,像是拆家一樣。
顧言的身體在微微發抖,他絕望地看著我,眼神里充滿了歉意。
我握住他的手,手心一片冰涼。
事已至此,再說什麼都晚了。
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,每一秒都是煎熬。
就在我以為一切都將敗露,準備迎接狂風暴雨的時候,晚飯時間,竟然到了。
張翠芬似乎也想在「審判」之前,維持她那可笑的「一家之主」的體面。
她冷著臉,讓保姆開飯。
於是,我們迎來了人生中最詭異、最漫長的一頓晚餐。
餐桌上,死一般的寂靜。
張翠芬的臉色陰沉得可怕,她一口沒動,只是死死地盯著我。
而我,則麻木地、機械地往嘴裡送著飯,食不知味。
突然,張翠芬夾起一塊她剛啃完的雞骨頭,「啪」地一聲,扔進了我的碗里。
「吃。」她從牙縫裡擠出一個字。
這大概是暴風雨來臨前,她最後一次享受這種羞辱我的快感。
我抬起頭,看著她那張因為憤怒而扭曲的臉,又看了看身邊面如死灰的顧言。
一股巨大的悲涼和不甘,從心底涌了上來。
我輸了。
輸得一敗塗地。
所有的隱忍,所有的謀劃,在這一刻,都成了一個笑話。
也好。
既然演不下去了,那就不演了。
我拿起筷子,夾起了那根骨頭。
但這一次,我沒有放進嘴裡。
我只是靜靜地看著它,臉上,緩緩地,露出了一絲詭異的微笑。
那是一個解脫的,瘋狂的,帶著毀滅氣息的笑容。
就在這時,臥室的門突然被撞開!
顧莉舉著一張紙,像發現了新大陸一樣,滿臉通紅地沖了出來,聲音因為激動而尖銳無比:
「媽!找到了!我找到了!你快看我在他們房間的床墊下面找到了什麼!是……是財產贈與協議!」

06
「財產贈與協議」六個字,如同一顆重磅炸彈,在死寂的餐廳里轟然引爆。
空氣瞬間凝固。
張翠芬臉上的得意和狠厲在剎那間褪去,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極致的震驚和難以置信。
她猛地從椅子上站起,動作快得不像一個年過半百的女人。
「你說什麼?拿過來!」她的聲音嘶啞而尖利。
顧莉三步並作兩步衝上前,將那張被她捏得有些發皺的紙「啪」地一下拍在餐桌上。
張翠芬顫抖著手,一把抓過那張紙。
她的目光像兩道利劍,死死地釘在紙面上。
當她看清上面「贈與人:顧言」、「受贈人:林晚」、「贈與財產:位於XX路XX號房產一套及個人信託基金叄佰萬元整」這些字眼時,她的瞳孔驟然收縮,呼吸都停滯了。
「顧言!」
一聲歇斯底里的尖叫劃破了寧靜。
張翠芬猛地抬起頭,那張保養得宜的臉因為極致的憤怒而扭曲變形,顯得格外猙獰。
她像一頭髮了瘋的母獅,揮舞著那張紙,沖向顧言。
「你這個畜生!白眼狼!我辛辛苦苦把你養這麼大,你竟然背著我,想把家產都送給這個狐狸精?!三百萬!你哪來的三百萬!啊?!」
她瘋狂地用那張紙抽打著顧言的臉和身體。
顧言下意識地抬手去擋,卻一動不動地站在原地,任由她發泄。
「媽!你別打了!」我下意識地喊出聲,想上前拉開她。
「你給我滾開!」張翠芬看到我,更是怒火攻心。
她一把推開顧言,轉而將目標對準了我。
她揚起手,一個巴掌就朝我的臉狠狠扇了過來,指甲上新做的紅色蔻丹在燈光下劃出一道刺目的厲芒。
「都是你這個賤人!是你攛掇我兒子的!我要打死你這個狐狸精!」
就在那巴掌即將落下的瞬間,一隻更有力的手,緊緊地攥住了她的手腕。
是顧言。
他擋在了我的身前,高大的身軀像一堵牆,將我嚴嚴實實地護在身後。
他的臉上還留著被紙張劃出的紅痕,但眼神卻不再是往日的懦弱和躲閃。
那是一種混雜著痛苦、決絕和徹底爆發的火焰。
「夠了!」他低吼著,聲音是從胸腔里迸發出來的,帶著巨大的迴響,「不准你動她!」
張翠芬愣住了。
這還是她那個一向對自己言聽計從的兒子嗎?
他竟然敢為了這個女人,跟自己動手?
「你……你敢攔我?」張翠芬氣得渾身發抖,「為了這個女人,你敢跟你媽動手?反了!真是反了天了!」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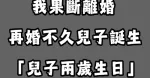
 武巧輝 • 7K次觀看
武巧輝 • 7K次觀看
 楓葉飛 • 4K次觀看
楓葉飛 • 4K次觀看














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