可轉念一想,她心情不好,買啥都不會高興。
算了,等她自己想開吧。
推開家門,家裡還是昨天那副樣子。
亂七八糟的。
顧清雅坐沙發上,正低頭看手機。
看見我進來,她放下手機,起身去了廚房。
我換好拖鞋,走到沙發前,看見茶几上放著一碗湯。
是媽送來的烏雞湯。
「媽來過了?」
我問。
「嗯。」
顧清雅在廚房應了聲。
我端起碗喝了一口,湯很鮮,味道正。
還是媽的手藝好。
「你喝了嗎?」
我問顧清雅。
「喝了。」
她聲音有點冷。
我隱約覺得不對勁,可又說不上來哪裡不對。
吃完飯,我坐沙發上看電視。
顧清雅收拾完廚房,抱著江念念坐在另一邊。
兩個人之間隔著一米遠,像隔著一道無形的牆。
電視里在放什麼,我根本沒看進去。
餘光總是飄向顧清雅。
她低著頭,輕輕拍著江念念的背。
孩子睡得很香,小臉蛋紅撲撲的。
「清雅。」
我突然開口。
「嗯?」
她沒抬頭。
我想說點什麼,可話到嘴邊又不知道該說啥。
算了,還是別說了。
說了估計又要吵。
晚上十點多,顧清雅抱著孩子回臥室睡覺。
我在客廳坐到快十二點,才關電視回房間。
顧清雅已經睡了,呼吸很平穩。
我輕手輕腳躺下,沒敢吵她。
就這樣,第一天過去了。
第二天,第三天,都差不多。
兩個人之間的氣氛越來越壓抑。
顧清雅不怎麼跟我說話了,我也懶得主動開口。
兩個人就像兩個陌生人,住在同一屋檐下。
02

周末那天,我難得休息。
本來打算在家好好陪陪顧清雅和孩子。
結果上午十點剛過,賀芳菊就提著大包小包來了。
「子墨,媽給你燉了排骨湯,還買了你愛吃的滷肉。」
媽進門就往廚房鑽。
顧清雅抱著江念念坐客廳,看見婆婆來了,臉色變了變,但還是禮貌地叫了聲:
「媽。」
「哎,清雅在家呢。」
賀芳菊頭也不回地應了聲,繼續在廚房忙活。
我起身想去幫忙,被媽推出來:
「去去去,你坐著。這點小事還用你動手?」
我只好又坐回沙發。
看見顧清雅表情不太對,我問:
「怎麼了?」
「沒事。」
她抱著孩子站起來:
「我去臥室。」
「吃完飯再去嘛。」
媽在廚房喊。
顧清雅沒回答,抱著孩子進臥室,還把門關上了。
賀芳菊從廚房出來,看了眼臥室門,皺眉:
「這孩子,怎麼又不高興了?」
「別管她,她心情不好。」
我說。
「心情不好也不能這樣啊。」
賀芳菊在圍裙上擦手:
「都當媽的人了,還這麼任性。」
我沒接話,心裡挺不舒服。
一邊是媽,一邊是老婆,兩頭都不好說。
中午吃飯時,我去叫顧清雅。
推開臥室門,她坐床上看手機。
江念念睡在旁邊。
「吃飯了。」
我說。
「我不餓,你們吃吧。」
她頭也不抬。
「你不餓也得吃點啊,媽做了你愛吃的紅燒排骨。」
我勸。
「我說了我不餓。」
她語氣很硬。
我站門口,進也不是,退也不是。
最後嘆口氣,轉身出去了。
餐桌上,賀芳菊給我夾了一大塊排骨:
「多吃點,工作辛苦,得補補身子。」
「謝謝媽。」
我埋頭吃飯。
「清雅不吃嗎?」
賀芳菊問。
「她說不餓。」
我含糊地說。
賀芳菊搖頭:
「這孩子,越來越不懂事了。都當媽了,還鬧脾氣。」
我聽著這話,心裡更堵。
吃完飯,賀芳菊收拾了下,臨走前又嘮叨幾句:
「子墨啊,你工作忙,媽理解。家裡的事你別太操心,有媽呢。清雅那邊,你多哄哄她,女人嘛,都愛聽好話。」
「知道了媽。」
我送媽到門口。
門剛關上,我就聽見臥室里傳來輕微的哭聲。
我走過去,推開門。
顧清雅背對著我,肩膀一抽一抽的。
「你哭什麼?」
我走過去。
她沒回答,只是哭得更厲害。
我站在床邊,不知道該說什麼。
腦子裡突然冒出一些畫面。
那是顧清雅生孩子那天。
我記得那天,我本來答應陪她去醫院。
可早上八點半,大客戶李總突然打電話,說要談那個跟了三個月的項目。
這個項目對公司很關鍵,對我的業績也很關鍵。
我跟顧清雅說:
「要不你先去醫院,我談完就過去。最多兩小時。」
顧清雅當時眼圈就紅了。
她預產期就是那天,羊水都破了。
可她還是點頭:
「那你快點來。」
我親了親她額頭:
「放心,很快的。」
可那場談判,整整談了四個半小時。
等我趕到醫院時,孩子都生完兩個多小時了。
護士把我領到病房,顧清雅躺在床上,臉色慘白如紙。
她看見我,眼淚無聲地流下來。
「對不起,路上堵車。」
我撒了個謊。
顧清雅沒說話,只是轉過頭去。
媽賀芳菊在旁邊抱著剛出生的江念念,看見我來了,笑著說:
「來了啊,你看,大胖丫頭!」
我走過去看了看孩子。
小小一團,皺巴巴的,哭聲很大。
「辛苦你了媽。」
我說。
「不辛苦不辛苦,這都是應該的。」
賀芳菊笑著:
「倒是清雅,生孩子受罪了。不過女人嘛,都得經歷這一關。」
顧清雅躺在床上,一句話也沒說。
那時候我沒多想。
覺得她可能是累了。
生孩子確實挺累的。
可現在想想,她當時的表情,好像不只是累那麼簡單。
是失望吧。
對我徹底失望。
還有坐月子那段時間。
媽來家裡幫忙照顧顧清雅。
我以為這樣挺好的,自己的媽,照顧自己的老婆,應該沒問題。
可事實證明,我想得太簡單了。
媽是老一輩人,講究老規矩。
坐月子不能開空調,不能洗頭,不能下床,不能吃水果。
顧清雅受不了。
那時候正是八月天,天氣熱得要命。
家裡不開空調,顧清雅每天汗津津的,睡都睡不好。
她跟我說過好幾次:
「子墨,能不能開空調?我快熱死了。」
我就去跟媽說。
媽說:
「坐月子怎麼能開空調?會落病根的!當年我生你的時候,比這還熱,不也扛過來了?」
我夾在中間,不知道該聽誰的。
最後還是聽了媽的。
畢竟,媽是過來人,她說的應該沒錯。
可顧清雅那段時間,臉色越來越差。
人也越來越沉默。
有天晚上,我加班回來,聽見衛生間傳來水聲。
推開門一看,顧清雅正在洗頭。
「你幹嘛?」
我嚇了一跳:
「媽說了坐月子不能洗頭。」
「我受不了了。」
顧清雅聲音很平靜:
「半個月沒洗頭,我覺得自己都餿了。」
「可是......」
「你到底站在誰那邊?」
顧清雅突然抬頭看我。
頭髮濕漉漉的,臉上也不知道是水還是淚。
我被她的眼神嚇到了。
那眼神,我從沒見過。
「我沒有站在誰那邊,我只是擔心你。」
我說。
「擔心我?」
顧清雅笑了,笑得特別苦:
「你擔心的是你媽生氣吧。」
我張了張嘴,不知道該說什麼。
那天晚上,兩人沒再說話。
顧清雅洗完頭,用吹風機吹乾,回了臥室。
第二天早上,媽發現了。
「清雅,你洗頭了?」
賀芳菊聲音有些嚴厲。
顧清雅點頭:
「嗯。」
「跟你說了多少次,坐月子不能洗頭!」
賀芳菊有些生氣:
「你這孩子,怎麼就不聽話?」
顧清雅低著頭,沒說話。
我站在旁邊,想說點什麼,可話到嘴邊又咽回去。
後來還有很多次類似的事。
顧清雅想吃水果,媽說坐月子不能吃涼的。
顧清雅想下床走走,媽說坐月子得多躺著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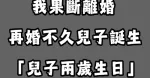
 武巧輝 • 7K次觀看
武巧輝 • 7K次觀看
 楓葉飛 • 4K次觀看
楓葉飛 • 4K次觀看














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