這個結果,我雖然不甘,但也只能接受。
畢竟,將主犯繩之以法,已經是我能爭取到的最好結局。
舅媽在李建國入獄後,帶著李俊回了鄉下老家,據說變賣了城裡的房子,用來賠償王倩倩家的彩禮和精神損失。
經此一役,李家算是徹底垮了。
那些曾經在群里對我口誅筆伐的親戚們,也都像人間蒸發了一樣,再也沒有人來煩我。
我的生活,似乎終於回歸了正軌。
公司里關於我的流言蜚語,也隨著時間的推移,漸漸平息。
我的工作能力,讓我重新贏得了同事們的尊重和領導的信任。
我用工作填滿所有的時間,升職,加薪,事業蒸蒸日上。
我買了新車,去了很多以前想去卻沒時間去的地方旅行。
我認識了新的朋友,開始學習烘焙和插花,努力地讓自己的生活變得豐富多彩。
許諾說,我像一株獲得了新生的植物,渾身都散發著光芒。
只有我自己知道,在無數個夜深人靜的夜晚,那道名為"親情"的傷疤,依然會隱隱作痛。
我偶爾會想起張愛華。
我想像著,她一個人,住在那個空蕩蕩的老房子裡,會是怎樣的光景。
她有沒有後悔過?
有沒有在某個瞬間,想起過我這個被她親手拋棄的女兒?
我以為,我們這輩子,都不會再有任何交集了。
直到兩年後的一天,我接到了一個來自鄉下醫院的電話。
電話是村委會主任打來的,他說,張愛華病重,查出來是肝癌晚期,醫生說,剩下的日子不多了。
"她……她一直念叨著你的名字。孩子,不管怎麼說,她都是你媽。你有時間的話,就回來看她最後一眼吧。"
掛了電話,我站在落地窗前,看著窗外的萬家燈火,久久沒有動彈。
我的心裡,五味雜陳。
有解脫,有快意,但更多的,是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複雜情緒。
恨嗎?
當然恨。
但她,終究是給了我生命的人。
許諾問我:"你去嗎?"
我沉默了很久,最終還是點了點頭。
"去。不是為了原諒,只是為了告別。"
我要去跟那個懦弱、自私、偏執的母親告別,也要去跟那個曾經卑微、隱忍、渴望母愛的自己,做一個最後的告別。
10
時隔兩年,我再次踏上了故鄉的土地。
鄉下的醫院條件很簡陋,空氣中瀰漫著消毒水和腐朽混合的難聞氣味。
我在病房裡見到了張愛華。
她躺在病床上,瘦得只剩下一把骨頭,蠟黃的臉上布滿了老年斑,渾濁的雙眼深深地凹陷下去。
如果不是那微弱起伏的胸口,我幾乎會以為她已經是一具屍體。
癌症的折磨,讓她早已不復當年的模樣。
看到我進來,她渾濁的眼珠動了動,似乎想說什麼,但只能發出"嗬嗬"的聲響,口水從歪斜的嘴角流下來。
我走上前,默默地抽出紙巾,幫她擦乾淨。
她的手,顫顫巍巍地從被子裡伸出來,想要抓住我。
那是一隻枯瘦如柴、布滿針眼的手。
我猶豫了一下,最終還是握住了它。
她的手冰冷,沒有一絲溫度,卻用盡了全身的力氣,緊緊地反握住我。
我們就這樣,沉默地對視著。
沒有歇斯底里的指責,沒有聲淚俱下的懺悔。
所有的是非對錯,恩怨情仇,在死亡面前,似乎都變得不再重要。
村委會主任說,這兩年,她過得很不好。
李建國坐牢後,她成了全村的笑柄,走到哪裡都有人戳脊梁骨。
她想去找李俊,但舅媽一家早就當她是個累贅,對她避之不及。
她一個人守著老房子,靠著一點微薄的低保過日子,直到被查出癌症。
她沒有錢治病,也無人照顧,只能在醫院裡,一天天地等死。
我在醫院陪了她三天。
這三天裡,我沒有跟她說一句話,只是默默地幫她擦身,喂她喝水,處理她失禁後的穢物。
我做得平靜而又麻木,像是在完成一項程序化的任務。
我不知道自己這樣做,究竟是出於血緣親情最後的憐憫,還是僅僅為了讓自己心安。
第三天晚上,她走了。
走的時候很安詳,握著我的手,慢慢地鬆開,那雙飽經滄桑的眼睛,最終永遠地閉上了。
我為她辦理了後事。
葬禮很簡單,除了我,沒有一個親戚前來弔唁。
我把她的骨灰,和我父親的,葬在了一起。
站在兩座並排的墓碑前,我忽然覺得,一切都結束了。
那個曾經帶給我無盡痛苦和傷害的家庭,那個曾經像枷鎖一樣捆綁著我的過去,都隨著這兩捧黃土,永遠地埋葬了。
離開家鄉的那天,天氣很好。
我坐在回城的車上,看著窗外飛速倒退的田野和村莊,手機響了。
是一個陌生的號碼。
我接了起來。
"喂,你好。"電話那頭,是一個溫潤而又禮貌的男聲。
"你好,請問是林微女士嗎?"
"是的,我是。您是?"
"我是XX律師事務所的張律師。我這裡,有一份張愛華女士留給您的遺囑,需要您過來確認一下。"
遺囑?
我愣住了。
張愛華能有什麼遺產留給我?
那個破舊的老房子嗎?
抱著一絲疑惑,我去了那家律師事務所。
張律師將一份文件遞給我。
那確實是一份遺囑,立於半年前,內容很簡單,卻讓我瞬間紅了眼眶。
遺囑里說,她自願將位於老家的那套房子,以及她名下所有的一張存摺,全部由我繼承。
房子不值錢,那張存摺,才是我情緒失控的根源。
存摺里,有十五萬零三百二十七塊。
後面附了一張信紙,是張愛華顫抖的筆跡。
"微微,這是你爸當年的撫恤金,剩下的錢。你舅舅當年賭博,並沒有把錢全部輸光,他還剩下這些。他把錢給了我,讓我藏起來,誰也別告訴。這些年,我一直沒敢動這筆錢。"
"媽對不起你,也對不起你爸。媽這輩子,活得不像個人,下輩子,給你當牛做馬,再來償還。"
"這些錢,本來就該是你的。現在,物歸原主了。"
信的最後,沒有落款,只有一個被淚水浸染得模糊不清的指印。
我拿著那封信,走出律師事務所,站在陽光下,淚流滿面。
原來,她並不是完全沒有心。
在她那被扭曲的親情觀和懦弱的性格深處,依然為我和爸爸,保留了最後的一絲愧疚和良知。
這筆遲到了二十多年的錢,並不能彌補什麼,也無法改變任何已經發生的事實。
但對我而言,它像一把鑰匙,打開了我心中最後一道枷鎖。
我釋然了。
我沒有要那筆錢,我以張愛華的名義,將它全部捐贈給了當地的希望小學。
我想,這或許是我爸,也希望看到的結局。
我的人生,翻開了新的一頁。
我依然是我,獨立、堅強、努力生活。
但我知道,從今天起,我的心裡,不再有恨。
陽光正好,微風不燥。
一切,都是新的開始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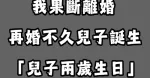
 武巧輝 • 7K次觀看
武巧輝 • 7K次觀看
 楓葉飛 • 4K次觀看
楓葉飛 • 4K次觀看














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