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們關心的是我每個月能拿多少工資,夠不夠付我那份"AA"的帳單。
他們也確實做到了他們口中的"獨立"。
家裡的開銷,他們會準時把帳單給我。
有一次我感冒了,發燒到三十九度,李娟給我端來一杯水和兩片藥,然後用微信給我轉了20塊錢,附言是:"媽,藥店買藥的錢,您收一下。"那一刻,我心裡的溫度,比我額頭的溫度還要涼。
他們自己的日子也過得緊巴巴。
王誠那三千二的工資,要付他們那一大家子的開銷,要養孩子,要還車貸,捉襟見肘。
李娟開始在網上找各種省錢攻略,買菜要等到晚上菜市場打折的時候去,家裡的燈泡全都換成了最節能的,給樂樂買衣服,也只敢在拼多多上淘那些幾十塊錢的。
家裡的氣氛越來越壓抑。
他們不再像以前那樣有說有笑了,常常因為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吵架。
比如李娟想給樂樂報個好點的興趣班,王誠就會說:"錢呢?你當錢是大風刮來的?"李娟就會反唇相譏:"你但凡有點本事,多掙點錢,我用得著這麼精打細算嗎?"
每當這時,我就默默地回到自己的房間,關上門。
我不想聽,也不想管。
這是他們自己選擇的路。
只有孫子樂樂,是這個冰冷家裡唯一的暖光。
他不懂什麼是AA制,他只知道我是他奶奶。
他會偷偷地把李娟給他買的好吃的,藏在口袋裡,然後跑到我房間,獻寶似的塞給我。
"奶奶,給你吃,這個巧克力可好吃了。"
我摸著他小小的腦袋,心裡又酸又軟。
孩子,等你長大了,會怎麼看你的父母呢?
有一次,我因為長時間站立,靜脈曲張犯了,腿疼得厲害,跟超市請了幾天假。
李娟看見了,不但沒有一句關心,反而提醒我:"媽,您請假了,這個月工資會不會少啊?下個月的帳單可別忘了。"
我看著她那張因為計較而顯得有些刻薄的臉,突然就笑了。
我慢慢地站起來,走到她面前,一字一句地對她說:"你放心,就算我不上班,我那八千八的退休金,也一分都不會少。我的那份,我死不了,就肯定會給你。倒是你們,可千萬要撐住了,別到時候,骨氣沒了,還得回來求我這個老婆子。"
李娟的臉,瞬間漲成了豬肝色。
03

我的話像一根刺,深深地扎進了李娟的心裡,也扎在了這個本就搖搖欲墜的家裡。
從那天起,她對我的態度愈發冷淡,連表面上的客氣都懶得維持了。
家裡的飯菜,她會精確地按照人頭來做,我的碗里,永遠不會多出一塊肉或一根青菜。
有時候我下班晚了,回到家,桌上只有冷冰冰的剩飯剩菜。
她和王誠,已經帶著樂樂吃過了。
王誠夾在我和他媳婦中間,左右為難。
他既覺得李娟做得有些過分,又拉不下臉來承認當初的"AA制"是個錯誤的決定。
他只能選擇沉默和逃避。
他下班回家的時間越來越晚,常常一身酒氣。
我知道,他在外面也不順心。
三千二的工資,在一個大城市裡,養活一個三口之家,還要維持所謂的"骨氣",其中的壓力,足以壓垮一個男人。
真正讓我徹底寒心的一件事,發生在一個冬天的夜裡。
那天我下班,外面下著凍雨,路面很滑。
我為了抄近路,走了一條小巷,結果腳下一滑,重重地摔在了地上。
我感覺自己的右腿傳來一陣鑽心的疼,掙扎了幾下,根本站不起來。
手機在摔倒的時候也飛了出去,螢幕碎成了蜘蛛網。
我躺在冰冷的地上,雨水打濕了我的棉衣,寒氣順著骨頭縫往裡鑽。
絕望中,我看到了一個路過的好心人,他幫我打了120,也用他的手機撥通了我家的電話。
是李娟接的。
我忍著劇痛,告訴她我摔了,可能骨折了,在XX路的小巷子裡。
電話那頭,李娟沉默了幾秒鐘,然後我聽到她問:"媽,那您還能動嗎?救護車過去要錢的,要不……我們打車過去接您?這樣能省點。"
我的心,在那一刻,比這冬夜的凍雨還要冷。
我疼得說不出話來。
旁邊的那個好心人似乎聽不下去了,他搶過電話,對著那邊吼道:"你們還有沒有良心!老太太都這樣了,你們還在算計錢!趕緊過來,我們在中心醫院等你們!"
我被送到了醫院,拍了片子,右腿脛骨骨裂。
醫生說需要住院觀察幾天。
當我躺在慘白的病床上,打著石膏,王誠和李娟才姍姍來遲。
王誠的臉上帶著一絲愧疚,而李娟,手裡拎著一網兜水果,臉上卻看不出太多的關切。
她進門第一句話就是:"媽,醫藥費花了多少?發票您收好了嗎?這個到時候咱們還是得按規矩來……"
"夠了!"我用盡全身力氣,打斷了她的話。
我看著王誠,一字一句地問,"王誠,你也是這麼想的嗎?你媽我躺在病床上,你們想的還是這個?"
王誠的臉瞬間漲得通紅,他低下頭,囁嚅著說:"媽,李娟她不是那個意思……"
"她就是那個意思!"我死死地盯著他,"你們當初跟我說AA,說要有骨氣,好,我認了。我六十歲的人,出去給人當促銷員,站得腿都腫了,我沒跟你們抱怨過一句。我摔斷了腿,你們想的還是錢!王誠,我問你,在你心裡,你媽這條腿,值多少錢?"
整個病房都安靜了下來。
隔壁床的病人和家屬都向我們投來異樣的目光。
王誠的頭埋得更低了,像個做錯事的孩子。
李娟的臉上青一陣白一陣,想反駁,卻又說不出話來。
那天晚上,他們走了之後,我一個人在病房裡,想了一整夜。
我想起了老伴,想起了王誠小時候的樣子,想起了我們一家人曾經的歡聲笑語。
那些溫暖的記憶,和眼前的冰冷現實,形成了無比尖銳的對比。
我終於明白,有些東西,一旦碎了,就再也回不去了。
我的心,也跟著我那條斷了的腿一起,徹底死了。
出院後,我做的第一件事,就是去銀行,把我這些年攢下的所有退休金,還有我做促銷員掙的錢,都存成了一個定期,密碼,只有我自己知道。
我不再對他們抱有任何幻想。
從今往後,我只為自己活。
04
腿傷養了三個月,這三個月里,王誠和李娟倒是"盡心盡力"地照顧我。
當然,這種照顧,是嚴格建立在AA制基礎上的。
他們請了護工,費用我們一人一半;他們給我燉了骨頭湯,食材的費用,李娟也一筆一筆記在了她那個小本子上。
我冷眼看著,一言不發,他們要錢,我就給。
我的順從,讓他們以為這件事就這麼翻篇了。
但他們不知道,我的心,已經變成了一塊捂不熱的石頭。
我臉上的笑容越來越少,話也越來越少。
我不再關心王誠工作順不順心,也不再問李娟家裡有什麼困難。
我每天就是吃飯、睡覺、做康復訓練,像一個設定好程序的機器人。
這個家,對我來說,已經成了一個只提供食宿的旅館。
時間一晃,就到了樂樂該上小學的年紀了。
這成了王誠和李娟最大的焦慮。
他們住的這個老破小,是我和老伴單位分的房子,對口的學校,是全市最差的菜場小學。
要想讓樂樂上個好學校,唯一的辦法,就是買學區房。
他們開始像瘋了一樣地研究各個區的學區政策,跑遍了所有中介公司。
然而,現實給了他們一記響亮的耳光。
重點小學的學區房,價格高得離譜。
一套五十平米的老破小,動輒就要上百萬。
別說全款,就連湊個首付,對他們來說都是天方夜譚。
家裡的爭吵變得更加頻繁,也更加激烈。
"都怪你,當初要是有遠見,早點買房子,現在至於這樣嗎?"李娟對著王誠嘶吼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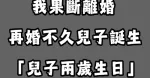
 武巧輝 • 7K次觀看
武巧輝 • 7K次觀看
 楓葉飛 • 4K次觀看
楓葉飛 • 4K次觀看














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