當冰冷的金屬門板在我身後嚴絲合縫地關上,將門外那一家人的咒罵與咆哮徹底隔絕時,我才發現自己的手在不受控制地顫抖。
那不是因為害怕,而是一種壓抑到極致後終於爆發的憤怒與快意。
門鎖的電子提示音清脆地響起,宣告著新主人權限的確立。
我靠在門上,聽著丈夫張昊在外面瘋狂地拍門,聽著婆婆用最惡毒的語言詛咒我,心中卻是一片前所未有的平靜。
這套房子,從房產證到每一塊地磚,都刻著我的名字,是我父母半生積蓄換來的底氣。
而如今,它也成了我婚姻的試金石,以及……墳墓。
01

我和張昊是大學同學,畢業後一同留在了這座繁華又擁擠的都市。
我們像無數普通情侶一樣,從合租小屋開始,一起擠早晚高峰的地鐵,一起在深夜的出租屋裡分享一碗泡麵,暢想著未來的美好。
張昊是個溫柔體貼的男人,他會記得我的生理期,為我準備紅糖水;會在我加班晚歸時,無論多晚都到地鐵口接我。
他對我無微不至的關懷,讓我相信,他就是那個可以託付一生的人。
他的家庭在鄰省的一個小縣城,父母都是普通工人,還有一個弟弟,早早輟學結了婚,日子過得緊巴巴。
張昊是全家的希望,也是他們口中「飛出山窩的金鳳凰」。
對於他時常要接濟家裡的行為,我雖然有時會覺得壓力大,但也表示理解,畢竟誰都有自己的親人需要照顧。
戀愛三年,我們到了談婚論嫁的年紀。
最大的難題,就是房子。
以我們倆當時的收入,想在這座一線城市買房,無異於痴人說夢。
張昊為此愁眉不展,不止一次跟我說,覺得委屈了我,是他沒本事。
看著他自責的模樣,我總是安慰他,說我們可以慢慢來,感情才是最重要的。
然而,我的父母卻不這麼想。
他們只有我一個女兒,思想比較傳統,總覺得女人必須有自己的安身立所,才不會在婚姻里受委屈。
在我媽幾次催促我將買房提上日程,並得知張昊家完全沒有能力支持首付後,她和我的父親做出了一個驚人的決定——他們願意拿出畢生積蓄,再賣掉一套老家的投資房,全款為我在這裡買一套兩居室,作為我的婚前財產。
當我把這個消息告訴張昊時,他先是震驚,隨即是狂喜。
他抱著我轉了好幾個圈,眼睛裡閃爍著淚光,激動地說:「薇薇,你爸媽就是我的再生父母!我發誓,這輩子一定好好對你,孝順他們!」看著他真誠的臉,我沉浸在幸福的泡沫里,絲毫沒有察覺到,命運的饋贈,早已在暗中標好了價格。
房子很快就定下來了,地段優越,裝修精緻,房產證上只寫了我一個人的名字。
爸媽辦完所有手續後,語重心生的地對我說:「薇薇,這不是爸媽要給你壓力,也不是信不過小張。只是人心隔肚皮,這套房子是你最後的底氣和退路。不管將來發生什麼,你都得有地方去,有家可回。」我當時覺得父母想多了,還笑著說他們太悲觀。
拿到鑰匙的那天,我和張昊在新房裡規划著未來,從家具的擺放到牆壁的顏色,每一個細節都充滿了甜蜜。
我們的婚禮很快也提上了日程,一切都在朝著最美好的方向發展。
然而,就在婚禮前一周,我未來的婆婆,王翠芬女士,帶著張昊的弟弟張強一家三口,浩浩蕩蕩地從老家殺了過來。
02
婆婆王翠芬的到來,像一顆投入平靜湖面的石子,瞬間打破了我們新婚前的甜蜜氛圍。
她一下火車,就對我噓寒問暖,拉著我的手誇我能幹,說張昊能娶到我是幾輩子修來的福氣。
她帶來的大包小包土特產堆滿了客廳,熱情得讓我有些招架不住。
張昊的弟弟張強則是一副吊兒郎當的樣子,弟媳李梅則顯得有些畏畏縮縮,他們五歲的兒子軍軍更是個混世魔王,一進門就穿著鞋在沙發上亂蹦亂跳。
我雖然心裡不悅,但想著他們是遠道而來的客人,又是為了參加我們的婚禮,便強壓下不適,熱情地招待他們。
我提前在附近的酒店給他們訂好了房間,想著這樣大家都能住得舒服些。
可當我提出送他們去酒店時,婆婆的臉瞬間就拉了下來。
「薇薇啊,你這是什麼意思?我們大老遠過來,不住在家裡,住什麼酒店?傳出去不讓人笑話我們娘倆生分嗎?」她一邊說,一邊用一種受傷的眼神看著張.
.
.
昊。
「媽,薇薇不是那個意思,她就是怕家裡住不下,委屈了你們。」張昊趕緊打圓場。
我心裡咯噔一下,這套房子是標準的兩室一廳,主臥我們自己住,次臥我原本打算做成書房兼客房,放了一張沙發床,偶爾招待朋友。
現在他們一來就是五個人,怎麼可能住得下?
「怎麼會住不下?」婆婆立刻提高了音量,仿佛受到了巨大的侮辱,「我和你爸,還有你弟一家,我們都是一家人,擠一擠怎麼了?我和你爸睡次臥,讓你弟他們一家三口在客廳打地鋪就行了。我們鄉下人,不講究這些!」她這話說得理直氣壯,完全沒把我當成這個房子的主人。
張昊的臉上露出了為難的神色,他拉了拉我的衣角,低聲說:「薇薇,要不就先這樣?我媽他們難得來一次,總不能讓他們覺得我們不歡迎他們吧。」我看著張昊祈求的眼神,又看了看婆婆那張不容置喙的臉,以及已經開始在客廳里追逐打鬧的孩子,第一次感到一種深深的無力。
我不想在新婚前就和未來的婆婆鬧僵,只能勉強點了點頭。
我的妥協,在他們看來,卻是理所當然。
當天晚上,家裡就成了一個混亂的戰場。
婆婆嫌棄我買的四件套不夠喜慶,非要把她帶來的大紅花被套換上。
張強夫婦則心安理得地把我們的客廳當成了他們的臥室,電視開到半夜,吃剩的零食袋子扔得滿地都是。
最讓我崩潰的是他們的兒子軍軍,不僅在我的白色牆壁上畫滿了蠟筆畫,還把我珍藏的一套絕版書撕得粉碎。
當我找弟媳李梅理論時,她只是不痛不癢地說了一句「他還是個孩子,你跟孩子計較什麼」,然後就沒了下文。
我向張昊抱怨,他卻總是那句話:「他們是鄉下人,習慣了,咱們多擔待點。為了我,忍一忍好嗎?」我看著他,突然覺得有些陌生。
那個曾經事事以我為先的男人,在面對他的家人時,似乎永遠只有一個「忍」字。
婚禮就在這樣一種混亂又壓抑的氛服中舉行了。
婚禮當天,婆婆當著所有親戚的面,大聲炫耀著這套房子,言語間仿佛這房子是她兒子張昊奮鬥得來的,對我父母的付出絕口不提。
我爸媽的臉色很難看,但為了我的婚禮,他們什麼都沒說。
我以為,等婚禮結束,他們總該回去了吧。
可我萬萬沒想到,這僅僅只是個開始。
03

婚禮結束後的第二天,我以為終於可以送走這尊大佛了,便試探性地問婆婆什麼時候回老家。
沒想到王翠芬一聽,眼淚說來就來,拉著張昊的手哭訴道:「兒啊,你是不是也嫌棄媽了?你這才剛結婚,就要把我們趕走。我和你爸把你拉扯這麼大,容易嗎?如今你出息了,在城裡有了大房子,就容不下我們這些土包子了?」她這一哭,張昊立刻就慌了神,抱著她連聲安慰:「媽,您說的這是什麼話,我怎麼會嫌棄您呢?薇薇也不是這個意思,她就是隨口問問。」說著,他轉過頭來,用一種責備的眼神看著我,仿佛我犯了什麼滔天大罪。
「那你倒是說說,你媳婦是什麼意思?」婆婆不依不饒,聲音尖利地指著我,「我們才來幾天啊?就這麼招人嫌?這可是我兒子的婚房,我們當爹媽的過來住幾天,難道還要看她一個外人的臉色?」「外人」兩個字像一根針,狠狠地扎進了我的心裡。
我氣得渾身發抖,這套房子,房產證上清清楚楚寫著我的名字,是我父母買給我的,什麼時候成了她兒子的婚房?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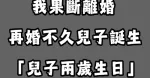
 武巧輝 • 7K次觀看
武巧輝 • 7K次觀看
 楓葉飛 • 4K次觀看
楓葉飛 • 4K次觀看














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