只會說「受不了就離婚」。
我說離婚的時候,根本沒想過她會當真。
我以為那只是氣話。
吵完架,過兩天就好了。
可我錯了。
她不是在鬧脾氣。
她是真的撐不下去了。
我靠著方向盤,眼淚止不住地流下來。
這時候,餘光瞟到副駕駛座位縫隙里有個硬硬的東西。
我伸手掏了掏,摸出一個白色的充電寶。
是顧清雅的。
外殼已經裂了一條縫,邊角也磨損了。
我準備隨手扔到后座,突然發現充電寶的夾層里塞著什麼。
拉開夾層,裡面有一張折得很小的紙條。
我展開紙條,借著路燈的光看上面的字。
紙上密密麻麻寫滿了字,筆跡有些潦草,像是在顫抖中寫下的。
開頭那行字讓我心裡一緊:
「如果有一天我真的撐不下去了,我想讓你知道......」
我的手開始劇烈顫抖。
深吸一口氣,繼續往下看。
「子墨,當你看到這些字的時候,我可能已經離開了。」
「不要找我,我不會回來了。」
「我想告訴你,我曾經有多愛你。」
「愛到可以為你放棄工作,放棄朋友,放棄所有的社交圈子。」
「愛到可以忍受你媽說的那些話,做的那些事。」
「愛到可以每天晚上一個人抱著孩子哭,還要等你回家。」
「可是,你知道嗎?愛是會被一點一點消耗殆盡的。」
我的視線開始模糊。
「生孩子那天,我在產房裡疼得要死。」
「護士問我家屬呢?」
「我說他馬上就來。」
「可你知道嗎?我等了整整五個小時。」
「五個小時啊,子墨。」
「我一個人躺在產床上,聽著隔壁產婦的丈夫在鼓勵她,陪她加油。」
「我多希望你也能在我身邊,哪怕只說一句話也好。」
「可你沒來。」
「等你終於出現的時候,孩子都生完兩個多小時了。」
「你說路上堵車。」
「可我聞到了你身上的煙味,還有那股很淡的香水味。」
「那是應酬時沾上的吧?」
「那一刻,我的心徹底涼了。」
淚水開始模糊我的視線。
我用手背胡亂擦了擦,繼續看。
「坐月子那段時間,你媽說的每一句話,做的每一件事,都像刀子一樣割在我心上。」
「她說我不會帶孩子。」
「她說我不會做家務。」
「她說我嬌氣,矯情,不像個當媽的人。」
「她說女人就該在家相夫教子,別想那些沒用的。」
「她在你面前一套,背著你又是另一套。」
「可你呢?」
「你從頭到尾只說了一句話:媽也是為你好。」
「江子墨,你知道那句話有多傷人嗎?」
我的手抖得更厲害了。
「我不是不理解老人,我只是希望你能站在我這邊。」
「哪怕只有一次也好。」
「可你沒有。」
「你永遠站在你媽那邊。」
「後來,我得了產後抑鬱症。」
這行字讓我整個人都僵住了。
產後抑鬱症?
她什麼時候得的?
為什麼我不知道?
我拚命回想,卻想不起任何徵兆。
不對。
不是沒有徵兆。
是我從來沒注意過。
她那段時間經常發獃。
經常一個人坐在陽台上,一坐就是很久。
經常半夜睡不著,在客廳走來走去。
可我都以為她只是帶孩子累了。
我繼續往下看。
「每天晚上,我都想從陽台跳下去。」
「真的,每天晚上。」
「我站在陽台上,看著樓下的街道,想著跳下去有多簡單。」
「就那麼一步,就解脫了。」
「可我不能。」
「因為念念還需要我。」
「她那么小,那麼脆弱。」
「如果我走了,她怎麼辦?」
「所以我告訴自己,再堅持一下。」
「等你忙完這陣子,一切都會好的。」
「我每天這樣告訴自己。」
「每天。」
「可我等來的是什麼?」
「是你說的那句:受不了就離婚!反正有我媽照顧我!」
我的心像被人狠狠捅了一刀。
那句話。
那句我隨口說出的氣話。
原來傷她那麼深。
「那一刻,我知道,我再也不能騙自己了。」
「你永遠不會改變。」
「你永遠不會看見我。」
「在你心裡,你媽永遠排在第一位。」
「工作排在第二位。」
「而我,大概排在很後面吧。」
「也許連孩子都比我重要。」
「所以,我走了。」
「不要找我,真的不要找我。」
「我需要時間療愈自己。」
「我需要離開這個讓我窒息的地方。」
「念念我會好好帶大。」
「也許多年以後,她會問起你。」
「我會告訴她,爸爸是個很好的人。」
「只是,我們不合適。」
「江子墨,再見了。」
「希望你能找到一個真正適合你的人。」
「一個不需要你改變,不需要你理解的人。」
「一個你媽喜歡的人。」
「一個不會給你添麻煩的人。」
「那樣的人,才能跟你好好過日子。」
「而我,做不到。」
「我只是個普通的女人。」
「我需要被愛,需要被看見,需要被理解。」
「可你給不了。」
「所以我們只能到這裡了。」
最後一行字,寫得特別重:
「顧清雅,2025年10月28日深夜,寫於你出差的第二天。」
紙條看完了。
我的眼淚已經止不住地往下流。
車窗外,天開始微微亮了。
晨曦的光線透過車窗,照在這張被淚水浸濕的紙條上。
我突然想起一個細節。
10月28日。
那天晚上我給她打電話。
她說「挺好的,你別擔心」。
聲音很平靜。
原來那時候,她已經寫好了這封信。
已經做好了離開的決定。
而我,還以為一切都好好的。
我什麼都不知道。
手機突然響了。
是個陌生號碼。
我抖著手接起來。
「喂?」
「江先生嗎?我是顧女士的朋友小雨。」
電話那頭傳來一個年輕女孩的聲音。
「清雅呢?她在哪?」
我急切地問。
「她讓我轉告你,離婚協議她已經簽好了。你簽完字寄到這個地址......」
「我不簽!」
我打斷她:
「我不會簽的!告訴她,我要見她!」
「江先生,清雅說了,她不想見你。」
小雨的聲音有些為難:
「她說,你們之間已經沒有什麼好說的了。」
「有!有很多話要說!」
我幾乎是喊出來的:
「我知道錯了!我真的知道錯了!」
「求你告訴我她在哪!」
電話那頭沉默了一會兒。
「江先生,我不能告訴你。」
小雨說:
「清雅來找我的時候,整個人瘦得不成樣子。」
「她抱著孩子,眼神空洞得嚇人。」
「我從來沒見過她那個樣子。」
「她說她真的撐不下去了。」
「她說如果再不離開,她怕自己會做傻事。」
「江先生,你知道她有多絕望嗎?」
「她說她想死。」
這句話像一記重錘,砸在我心上。
「她......她說什麼?」
我的聲音在顫抖。
「她說她想死。」
小雨重複了一遍:
「她說每天晚上都想從陽台跳下去。」
「她說如果不是因為孩子,她可能早就這麼做了。」
「江先生,你知道一個人要絕望到什麼程度,才會說出這樣的話?」
我說不出話來。
喉嚨像被什麼東西堵住了。
「我作為她的朋友,真的不忍心看她繼續這樣下去。」
小雨的聲音裡帶著哭腔:
「所以我支持她離開。」
「離開你,離開那個讓她痛苦的家。」
「江先生,如果你真的愛她,就放她走吧。」
「讓她好好活下去。」
說完,電話掛斷了。
我呆呆地坐在車裡。
腦子裡全是小雨說的那句話。
「她說她想死。」
顧清雅想死。
我的妻子,想死。
而我,竟然什麼都不知道。
我靠著方向盤,開始嚎啕大哭。
哭得整個人都在顫抖。
我終於明白了。
明白她為什麼會走。
明白她說的「你從來沒看見過我」是什麼意思。
我看見的,永遠只是她在做什麼。
卻從來沒看見,她的心有多痛。
她那麼愛我。
愛到可以為我放棄一切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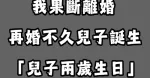
 武巧輝 • 7K次觀看
武巧輝 • 7K次觀看
 楓葉飛 • 4K次觀看
楓葉飛 • 4K次觀看




















